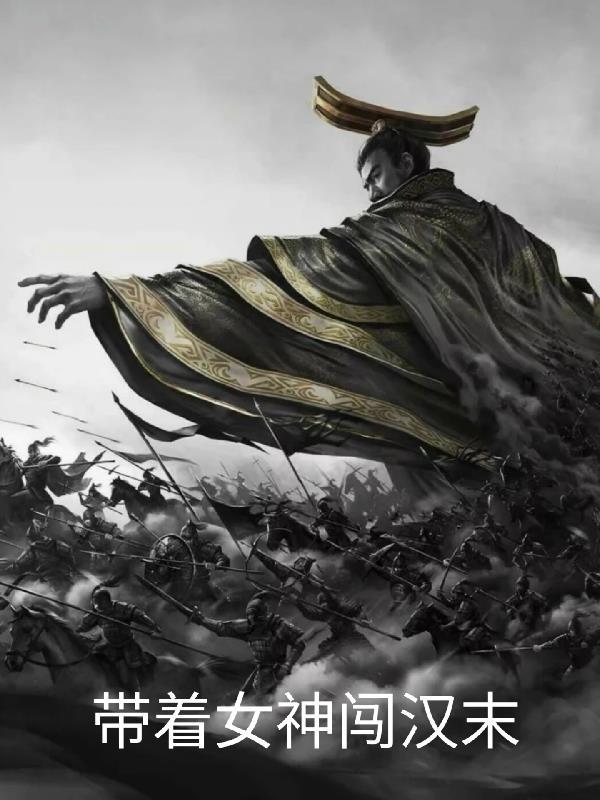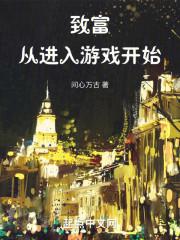风云小说>罗伯特·麦基虚构艺术三部曲 epub > PART ONE 对白的艺术(第6页)
PART ONE 对白的艺术(第6页)
关于能“演”就不要“说”的忠告仅适用于行动场景里的戏剧性对白。有技巧的直接讲述,无论是用在文学、舞台、银幕,通过叙事对白还是第三人称视角,都有两个重要功用:速度和对位。
速度
叙述可用几个很快的字眼就容纳很多信息,让观众读者马上了解并往下走。内心独白能在眨眼间将潜文本变为文本,角色与自己的对话则能自由联想诸多回忆,或者从潜意识中闪出若干影像。这种处理文字优美,可用一个句子就带动感情。举例说,名作家马尔克斯[39]的小说《百年孤独》中:“许多年后,面对行刑队,布恩迪亚将军回忆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就是快速生动的直接讲述,简短一句话展现复杂浓缩的影像。
不过,叙述被拍出来后常常成了“后来……后来……后来”式的无趣解说,只是为了抛出信息。这种方式偷懒地用“说”取代了费力的“演”。创作使复杂人物戏剧化的对白场景需要才华、知识和想象力,然而写一堆挤满了字的叙述只需要一个键盘。
想要将叙述式的解说改写成戏剧化的场景,必得启用以下两个技巧:
第一,改写,将“后来……后来……后来”转换成戏剧化的“我说他说”叙述场景。让叙述者
(无论是文字、舞台的第一人称或银幕上的旁白)可以从回忆中逐字演出场景对白,或使用非直接对白进行暗示。
flix(美国在线视频公司)的电视剧《纸牌屋》就经常改写非直接对白场景。凯文·史派西饰演的弗兰西斯·安德伍德频繁转向摄影机,像教授对着观众讲政治交涉课一样说话。安德伍德通过分析他自己和另一个角色唐纳德使解说戏剧化,在以下隐喻场景中,仅用两句台词就演出了唐纳德的性格缺陷:
“殉道者最渴望的就是一把会劈向他的宝剑,所以你就削好木剑,对准角度,然后,3、2、1……”
在下一个节拍中,就像安德伍德预言的一样,唐纳德为安德伍德的不当行为代而受罪。
第二,制造内在冲突:安排一个自己对自己的冲突,让叙述故事的角色与另一个自己争辩。两个电影例子:马丁·斯科塞斯《穿梭阴阳界》[40]里的角色皮尔斯(尼古拉斯·凯奇扮演)、鲍勃·克拉克《圣诞故事》[41]中的成年帕克(金·谢泼德扮演)。
对位
根据我的经验,最能丰富故事的叙事技巧就是对位。比起用叙述者讲故事,作家有时会让故事戏剧化,让一个叙述者反对或反讽故事主题。他们会用机智性嘲讽戏剧性,或用戏剧性深化嘲弄。他们让个人与社会对位,或让社会与个人对位,来表达一个声音。
举例来说
,约翰·福尔斯的后现代、历史性、反小说的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42],故事有一半在戏剧化维多利亚时代士绅史密森迷恋声名狼藉的女家庭教师萨拉·伍德拉夫的故事,然而,穿插其中的却是一个了解十九世纪文化和阶级冲突,以及它们如何颠覆史密森与萨拉情史的叙述者。一次又一次的对位应用后,叙述者辩称十九世纪的环境让没有生计的女人只有痛苦没有爱情。
其他例子:《你妈妈也一样》里,旁白叙述者不时提醒观众有关墨西哥的社会痛楚,以作为成长主题戏剧的对位。伍迪·艾伦聪明的作品《安妮·霍尔》也是用叙述旁白来对位主角的自我猜疑。还有塞缪尔·贝克特的独幕剧《喜剧》[43],则是由三个在瓮里伸出头来的角色,凝视观众,用三方的对位法叙述他们看似混乱的思绪。
叙述体小说是直接讲述法的天然媒介。小说与短篇故事作者可以按他们希望的直白方式将解说放置在前景,只要文笔引人,也可尽情延展。比方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场就用对位解说抓住观众的好奇心:
“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那是信仰的时期,也是破灭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之春,也是绝望之冬。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都正
走向天堂,我们都正走向另一方向……”
请注意,狄更斯用第三人称全知叙述法中的“我们”,让读者被卷入故事中。比较一下另一方法,用第一人称“我”的方式,如拉尔夫·埃里森[44]的《看不见的人》:
“我是个看不见的人。不,我不是埃德加·爱伦·坡笔下那种阴森鬼魅,也不是好莱坞电影里那种鬼魂。我是一有血有肉有骨有筋的人——甚至可以说我还有思想。我是个看不见的人,这么说吧,因为人们拒绝看到我。就好像你们有时在马戏班垫场戏里会看到的无头身体,我似乎被周遭坚硬、扭曲的镜子包围了起来。当人们走近我,他们只看到我的周围、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想象虚构——真的,他们看到一切东西,只看不见我。”
在这些篇目之后,狄更斯和埃里森都开始用戏剧化的场景表达,但有些文学作家却不这么做。他们反而用长篇累牍的直接叙述,而绝不将事件演绎出来。
我们想想,以上两段文字你如何将之处理成包含对白的戏剧场景?理论上它仍是可行的,莎士比亚就做得到,但一定很费力吧?为读者写,叙述确实可以创造奇妙的佳作。但若为演员而写,就完全相反了。
理想来说,在舞台和影视表演中,信息应该由观众从听到的话中不知不觉地得到。我们知道,要将解说做到不知不觉地传达必须依靠耐心
、才华和技巧。缺乏以上三种品质,有些粗疏没有才华的编剧就只能强迫观众接收信息,并乞求大家谅解。
○强行解说
打从有电影开始,电影人就会把巨大的标题,如“开战!”等事件的报纸画面插入镜头。他们已让观众习惯于听看新闻,准时得到应有资讯。快速的蒙太奇画面和分割画面组合,会使银幕用最短的时间充溢出最多的信息。电影人将这种解说手法合理化,认为只要信息快闪而过,观众就不会觉得烦闷。这观念是不对的。
同样的思维也常出现在开场的滚动片头,如《星球大战》(快速提供了信息又带着庄严的味道),或者《一条叫旺达的鱼》的片尾。当惊悚片与时间竞赛,从一地跳到另一地,他们也常将地名和时间叠印在定场镜头上。这种方法使小资讯常留脑中。如果用有力的影像或很快的字幕信息打断叙事,故事就会像摔了一跤之后往前走,观众也会耸肩略过。
毫无修饰地将大量与角色或场景无关的事实塞在对白当中可是会遭到观众讨厌的。这种无效的写作迫使角色互相诉说彼此已知的事实,使故事节奏像跳过高栏杆后,一股脑摔进煤灰,再也爬不起来。
举例:
内景奢华大房间——日
约翰和珍坐在有流苏的沙发上,啜饮马丁尼酒。
约翰
噢天哪,亲爱的,咱俩认识和相爱多久了!哇,超过二十年了,是
吧?
珍
是啊,从我们大学开始,你那兄弟会开派对请我们女子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人参加,你们那么有钱,我们那穷妹妹会称你们亿万、兆……有钱人。
约翰
(看着四周豪宅内景)
对啊,然后我完全没拿到遗产,但我俩一块重新打拼才美梦成真。对吧?我的小特洛兹基伊特?
这段对话告诉观众七个事实:这对男女很有钱,约四十岁,在大学兄弟会妹妹会社团里相识,男的出生口含金匙,女的出身贫困,而且双方以往政治观南辕北辙,但现在已经一致,多年来两人发展出一种甜腻到死的对话方式。
这场景很虚,对白微弱,因为写法非常不诚实。角色不在做似乎他们应做之事,他俩像在怀念过往,事实上他们却在提供解说,使偷听中的观众可以听懂信息。
前面提过,文学作家可以避免这些虚假场景,仅短短勾勒婚姻史,用怡人的风格将事实串接在一起。可以的话,文学作家可以在限度内,给予读者他们应知的信息。有些剧作家和影视编剧也会学小说家用叙述手法,但几乎无一例外,这种在舞台上的直接述说或者银幕旁白,其解说绝对无法比拟戏剧性对白的知性力量或情感影响力。
想理解这一点,请你自己做个如武器般呈现的练习。重写上面那一场戏,使两个角色如战斗中的武器般扔出信息,让一个角色强迫另一角色做他不愿
做的事。
然后再来一遍,这一次,将有些事实放在诱导的场景内,一个角色用他知道的信息为武器,巧妙地诱使另一角色做他不想做的事。
最后再重写一遍,使信息隐藏起来,使角色的行为有可信性。换句话说,用冲突或诱惑迷惑读者观众,使他应知的信息悄悄钻进脑中。
◎角色塑造
对白的第二个功能就是为剧中每个角色创造、表达一个可识别的角色塑造。
人的本质可有效地分成两大块:外表(这个人可能是什么样的人)vs真实(这个人真正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作家设计角色就朝角色塑造(characterization)和性格真相(truecharacter)两个方向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