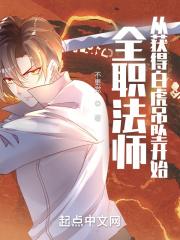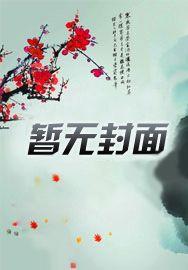风云小说>远遁怎么读音 > 第57章 吹尽狂沙始到金(第6页)
第57章 吹尽狂沙始到金(第6页)
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赠李司空妓》
李绅曾当过司空(负责水利、营建方面的工作),这里是说李绅见惯了这种大排场,而刘禹锡见之却非常不忍。
“司空见惯”这句成语,从此不胫而走。能够写出成语的人,都不简单。
对权贵,刘禹锡一身正气,嫉恶如仇。对百姓,他倡导“功利存乎人民”。无论身居何处,刘禹锡都能守正不阿,重土爱民,兴教重学。他的执政能力终于在苏州得到了应有的肯定和褒扬。浙西观察使王璠fán在苏州看到刘禹锡杰出的政绩后,在考课中将他列为“政最”——这是和平时期大唐地方官员极少能得到的荣誉。朝廷特加褒奖,赐刘禹锡紫袍、金鱼袋,以示荣宠。
与朝廷所加紫金鱼袋相比,苏州百姓对刘禹锡的爱戴,才是令他最为欣慰的奖赏。大和八年,刘禹锡在苏州百姓夹道相送的哭声中,在“流水阊门外,秋风吹柳条。从来送客处,今日自魂销”(《别苏州二首》其二)的不舍和惆怅中,调任汝州(现在的HEN省汝州市)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道防御使(负责汝州行政、军事事务)。此后,苏州百姓自发地建起三贤祠,以供奉曾为苏州做出巨大贡献的韦应物、白居易和刘禹锡,千年以降,香火不断。
转过年来,已经习惯了闲居生活的白居易以病为由,拒绝授其同州(现在的SX省WN市大荔县)刺史的任命。这顶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防御、长春宫等使的乌纱帽,又落到了刘禹锡头上。
同州已连遭四年大旱。刘禹锡上任后,除赈灾放粮外,就是引众赴山祈雨。祈雨途中,因年事渐高(已六十五岁),不慎脚部受损,只好在府衙稍歇,并无多事。
不久,“甘露事变”爆发。刘禹锡的好友王涯、王璠在事变中被杀。刘禹锡深感凭一己之力无法力挽狂澜,心生退意。在同州未满一年,他便以足疾辞官,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闲职,在洛阳上班)。
洛阳是陪都,到这里来的中央籍官员基本上都是闲职。
刘禹锡在一天天地老去。
那么,刘禹锡放弃他的志向了吗
绝对没有!
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李德裕回京任宰相。他将咏怀壮志的《秋声赋》寄给刘禹锡,刘禹锡在回赠的《秋声赋》中有句云:“骥伏枥而已老,鹰在韝gōu而有情。聆朔风而心动,盼天籁而神惊。力将痑tān兮足受绁xiè,犹奋迅于秋声!”
刘禹锡自比老骥伏枥,但仍想着驰骋千里;自比雄鹰受缚,但仍想着展翅高飞。已是古稀之年,尽管一生之中难得顺利,但是刘禹锡依然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和激情,他的生命充满了活力。这首激情昂扬的秋歌,也是刘禹锡一生鼓角长鸣的战歌。
这一日,白居易邀刘禹锡到邙山聚会。此前数日,白居易曾命人将新作《咏老赠梦得》传书刘禹锡。诗中写道:
与君俱老也,自问老何如。
眼涩夜先卧,头慵朝未梳。
有时扶杖出,尽日闭门居。
懒照新磨镜,休看小字书。
情于故人重,迹共少年疏。
唯是闲谈兴,相逢尚有馀。
谈及此诗,刘禹锡见白居易热泪盈眶,宽慰道:“乐天何以如此悲伤生老病死,乃天之道耶。既是天道,你我又何须伤怀老则老矣,却仍可当家国事,岂不闻魏武‘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诗那姜太公垂钓于渭水之畔时,不过也是你我如今之岁数。”说罢,刘禹锡和诗一首:
人谁不顾老,老去有谁怜。
身瘦带频减,发稀冠自偏。
废书缘惜眼,多灸为随年。
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
细思皆幸矣,下此便翛然。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酬乐天咏老见示》
如果单就这两首咏老诗而论,刘禹锡的胸襟和气度远远超过白居易了。
白居易谢刘禹锡道:“梦得不愧诗中豪者,一首诗便撞开了老朽心结!梦得所言甚是,人孰无老纵如老朽诗中所言疾病缠身又能如何经历了丰富的人生,看的人、看的事多了,自然格外看得准。细细想来,你我确实已经比很多人幸运。最妙是梦得末尾两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你我虽半生坎坷,但如今朝廷对你我礼敬有加,晚辈后生常常登门,或讨教文章,或干谒求荐,正如晚霞般照耀天地。君之乐观旷达,世所罕见。老朽可算是见识了!”
其实刘禹锡不但在胸怀上有时超于白居易,在艺术创作上有时甚至压过李白一筹。
传说昔日有人往楚地经年不还,其妻登山望夫归来,遂化为石。李白曾作《姑孰十咏》,其中有诗曰《望夫山》:
颙望临碧空,怨情感离别。
江草不知愁,岩花但争发。
云山万重隔,音信千里绝。
春去秋复来,相思几时歇。
刘禹锡当年离和州任时曾作《望夫石》,其境界远超李太白:
终日望夫夫不归,化为孤石苦相思。
望来已是几千载,只似当时初望时。
刘禹锡就像这个妇人千百年如一日地在那里等待丈夫归来一样,他无时无刻不在期望大唐的复兴,终生朝着兼济天下、拯救苍生的目标迈进,且始终永葆初心,不变本色。
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秋,刘禹锡溘然长逝于洛阳宅中,官终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后追赠兵部尚书,葬于祖坟荥阳檀山原。
释迦牟尼诞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我”代表“我识”,即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保持本我更重要。人什么都可以不在乎,唯独不能忘记自己的本心。刘禹锡正是将这种唯我独尊的浪漫主义情怀融入到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当中,亘古地激发着民族的正能量,永远激励着我们。
注:①关于《陋室铭》的作者、写作时间及地点学界尚存争议,笔者暂定为刘禹锡在和州任上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