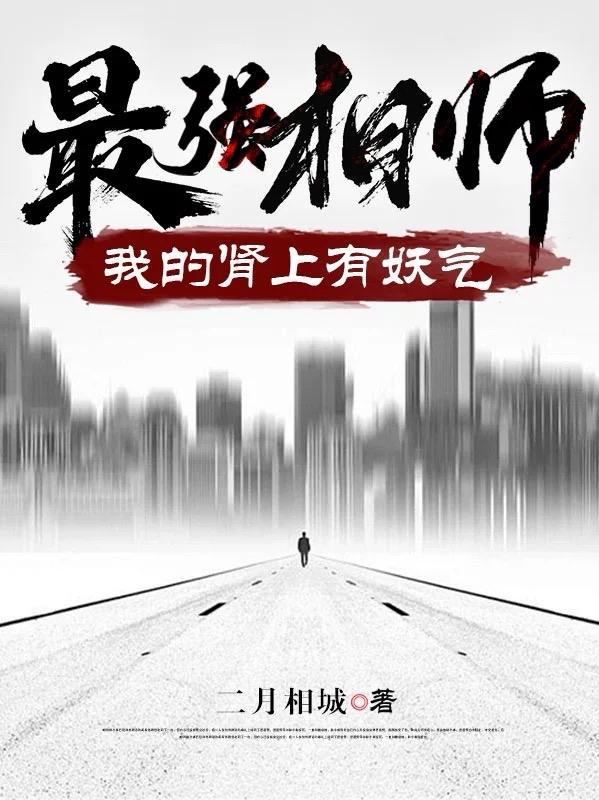风云小说>全网磕我们的过期糖百度 > 第212章(第1页)
第212章(第1页)
这人背对着楚言,脑袋后面虽然束着头发,但一看就是个男的,因为那肩膀的宽度,腿的长度,露出的小臂上的肌肉线条和凸起的青色血管走势,虽然弓着身子,扒着梯子,但肉眼可见的少说不会低于一米八。
他手里握着一把野外露营用的军刀,手起刀落,不过下,就在橡木桶边沿豁出一道口子。紫红色的葡萄酒沿着木桶壁微细地溢了出来,那人立马伸出一只手兜住了,另一只手摸到事先放在梯子上的高脚杯,一边换手去接葡萄酒,一边伸出舌头把手里兜住的酒液舔了个干净。
待高脚杯里的酒注了大半杯,那人不知从哪儿掏出来一块工程用胶布,对着橡木桶上那道口子啪唧一拍,转身从梯子上纵身一跃,落到地上,手中杯子里的葡萄酒竟然一滴都没洒在地上。
那人这才注意到自己身后一直站着一个人,抬起脸,明目张胆地用极其直白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楚言。
楚言在看见那人正脸时不可抑制地倒吸了一口气。好伟大的一张脸。
上小学那会儿大家都看《流星花园》,日版漫画直译过来叫做《花一样的男子》。当年楚言只觉得肉麻,男的要是像花一样,那还不是个娘炮?他们班当时就有个那样的男生,常常被人骂是“二椅子”。
面对眼前这个人,楚言第一次相信,原来这世界上真的有花一样的男子,美而不娘,艳而不妖。
这人皮肤白的发光,鼻子生得极好,充满了男性的英气,再配上精致的眉毛眼睛嘴巴,顶级的画师若是没见过本人,也想象不出这样的美貌。
他打量着楚言,之后没来由的噗嗤一声笑了,问了句:“中国人?”
一般小贼被抓住偷酒会有的紧张和尴尬在这个人脸上半分都没有,反而神色十分松弛和愉快。
楚言反问他:“你是混血?”
对方毫不掩饰地自报家门:“我爷爷是拉脱维亚人。”
“怪不得,拉脱维亚人几乎都是蓝眼睛。”
从这人过分优秀的骨相,外加瞳孔里微微透出的蓝色,楚言早就猜出了个大概。猛一看是亚洲人,实际最少14混血。
这位蓝眼睛举起手中的红酒杯,晃了晃,“你也是来品酒的?”
楚言一愣,心说这人脸皮可真是厚,“你管这叫‘品酒’?我们那儿管这叫‘偷’。”
蓝眼睛的目光落在楚言的手上,坦然地笑道:“哦,那你拿着作案工具干吗?该不会是来酒窖漱口的吧!”
楚言低头一看,自己手里居然握着一只玻璃杯,他心不在焉,估摸着是从影音室出来的时候顺手拿出来的。他反观了一下自己,卫衣卫裤,脚上穿着双一脚蹬,手里拿着个空杯子,确实不像是这座庄园的主人或嘉宾,看上去和这个小贼没什么区别。
他还来不及回怼那个偷酒的,对方便一把抓着他的手腕抬起来,往他的杯子里倒了一些红酒,但是抠门的只给没过杯底一点点。倒完酒,那人二话不说便一扭头,悠哉地坐在一旁台阶上,兀自喝起酒来。
楚言觉得这人可太有意思了,他不记得今天宾客里有这么一号人物。也对,要是宾客的话,晚上宴会的时候就可以大大方方地饮酒,哪里需要废这个劲?庄园里的佣人楚言都见过,他不禁走过去,坐在了这人的旁边,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你觉得呢?”
“不知道,”楚言打量着他的穿着,磨旧了的衬衫和水洗白的牛仔裤,“看着像个……嗯,像个艺术家。”
对方带着笑意歪了歪头,“你可以说得更直接一些。”
楚言:“反正看着不像富人。”
那人仿佛对楚言的“冒犯”十分满意,之后一仰面,居然把杯里的红酒给一口闷了,似乎在用行动证实,他是个连品酒都不会的平头百姓,而且连装都懒得装。
喝完,他用手指擦了擦嘴角宝石红的酒液,不以为然地说:“富人不过就是有钱的穷人罢了。这酒也就那样儿,没意思。”
这话好像是在嘲弄这座庄园的主人,楚言感觉心里不太舒服,开口道:“那是你不会品,这么长年份的酒刚从橡木桶里拿出来是不能直接喝的,需要醒酒。这样才能让葡萄酒和因为陈年产生的带苦味儿的碎渣分离开来,而且葡萄酒也需要和空气接触,加速氧化,就像呼吸一样。你刚才那样,等于是把尸体囫囵吞了。”
这一番科普应该能让这个偷酒贼心服口服吧,富人的这些玩意也不是全然没有价值,他牛嚼牡丹,反咬这好酒没意思,必须要给他个教训。
楚言等着看对方吃瘪,或者至少也要流露一丝尴尬的眼神,让他出出气。没想到那人毫无反应,盯着他的杯子,只是淡淡地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就瞬间把他给打蔫儿了。
“你这杯子挺好看的,别人送的?”
这杯子是易卿尘搬离帝京公馆时留下的,是他那次去景德镇亲手从吹玻璃开始给易卿尘做的。易卿尘不要的杯子,楚言却舍不得丢,一路带来了法国,天天不离手。
他苦笑了一下,任谁都能看出他突然的失意。
“我前男友留下不要的。”
虽然他已经把易卿尘的身份包装成了“前男友”,没说“我死皮赖脸追了几年又看不上我的人”,算是挽尊,可这句话一出,蓝眼睛还是给了他一个可恶的同情的眼神。
楚言一个窝火,也一仰颏,把杯子里的酒全灌进了喉咙。
“怎么样,尸体味道怎么样?”
这人虽然脸好看,嘴巴也挺毒的,而且看这架势,还是个有仇必报不吃亏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