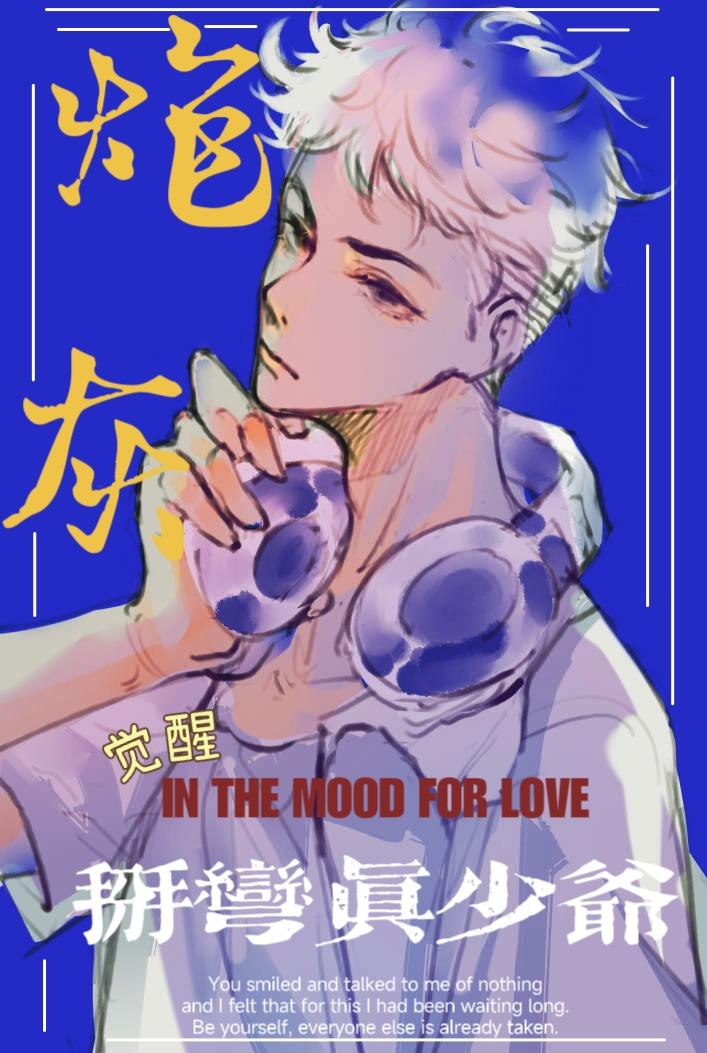风云小说>一个妇女的日记是经典吗 > 第一百零七章 岁月赠别离(第2页)
第一百零七章 岁月赠别离(第2页)
他们路过时,小白,阿骆打趣她戴眼镜,沈用手去打她的眼镜,嗔责她,我竟恨得连看也不想看他们一眼。
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又在那里挑选衣服,我装着没看见,他摇单车铃,我与他笑笑。
她却叫我帮她审美,我不得不走出去说那件衣服不值那么多钱,还问他为什么在这里买?他说又不出乐昌,然后我进了门市部。
我是外露的,而他也是敏感的。
而她却比之前友善多了,我又好象不好去嫉妒了。
他们无声的消失后,我真恨自己,恨死自己。
我的怨恨来于没有人倾诉,没有谁来关心安慰我帮助我,我又是多么的无助。
他们虽然不能帮我什么,但在精神上我是需要他与韩的,而他们的心里就只有恋人了,再没有我了。
我仍在不停的恨着,恨他,恨我自己,恨所有的人,恨这个世界。
脑门心又疼了,不是得了脑膜炎吧?要是,死了也可惜吧?连初吻也没尝过,死了不是不划算?我就又害怕死。
躺在床上无聊时,觉得死又有什么怕呢?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我只是按着人生的轨迹,循着生活的顺序过下去了。
我想在二十二岁去寻觅,恋爱,二十四五岁结婚,不想二十二三岁就走入婚姻,可我,好象等到那个年岁也很难呀。
人生,真的有那么难捱吗?
下班后,走在路上,都觉孤单单的,想去礼堂看他们布置装饰得怎样了?去找韩燕,她还没下班。
我只站在礼堂外面,没有进去看,说心里话,我一点也不想去扮演那个失意的角色,也想不到自己快要调走了,还对他有依赖,竟有了妒嫉和失意,真的,我还能对他象朋友一样潇洒吗?但愿他不再出现吧。当然更不愿他们双双出现。
明天,明天又是怎样的一天呢?再不快乐,也开联欢呵。
九o年十二月三十日阴
盘点时,并没有换人。
我的担忧是多余的,不强求,顺其自然不是很好吗?
在盘点时,我问吴志坚,今晚不去唱一歌吗?
他说:“你去嘛,你是团员,不起带头作用,为供销社争光。”
他说单位搞什么活动都是输的,又没人管,如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没有一个行的。他称说自己的乒乓球是特长,再后说唱歌人老了声音也老了。说以前他比赛是没能唱到高音。
我问:“那你今晚唱什么歌?”
他说:“唱《弯弯的月亮》但没伴奏带。”
邓建宇来买红纸,我才知我们单位没有节目,通知早下去了没人管。
晚上洗澡洗头。问吴去不去唱歌?若不去我去,他说他去,还要借录音带伴奏。我说去哪儿借,骆说去张那里借,不忿得自己单位连一个节目也没有。
上楼来,化妆,搽白粉,描眉,然后去廊剪,把刘海吹得翘翘的,后去叫韩,她答应陪我一起去的。
人很多,没位坐,我们走去后台,引人注目。严和张当评委还注意了我们,走下来又见张和吴。
晚会开始了,一出场的是严,他配着音乐说唱《外面的世界》一会儿却唱:“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还没等唱完,我们就又下去,韩说要走,我说等我有位置坐才准她走,这样就一起去了最前面,张他们坐的地方。韩拿了张凳子给我就走了。
节目是舞蹈,独唱,小品,邹永忠和陈小娟主持。
严刚站在我旁边,坐我的那张凳子,张国栋去唱歌时我就去坐他的凳子,然后我们就在聊天。
“你就唱一歌吗?”
“不,还有一个节目。”
“唱《拒绝再玩》吗?”我拿着那张节目单,把“玩”字说成平日随口说的语法,张就纠正过来,严就笑笑。
在张唱完歌走下来就赶我走,我说没礼貌,他问我这样打扮得不得体?唱得好不好听?我说不好听。他说是他唱的歌我都说不好听的啦。
轮到严的节目《拒绝再玩》时,他那么文质彬彬,斯斯文文的人会跳霹雳舞是我所不能预料的,尽管他在舞台上尽情的摇摆歌唱,但给我的感觉仍还是斯文沉稳。邹说他唱歌有潜质的。我觉得他们都会弹吉他,音乐知识都是比我们不会唱歌的人强。
最后是严和张合唱《卡拉永远ok》
赖冬娣唱:“我们亚洲……”得了第四名。
严刚得了第三名,第一名是一个跳抽筋舞的男孩。
事实上我己经站得很累了,但却没有走的意思,觉得快乐是别人的,只能分享而不能一起快乐。看见黎晓兰和邓在跳双人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