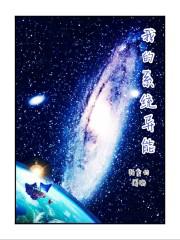风云小说>电影意志的考验完整版 > 扶乩书写(第1页)
扶乩书写(第1页)
扶乩书写#pageNote#0
一
史蜀君导演于2016年2月间去世,之后并未引发业内更多追思与怀念活动。固然,她的电影生涯主要在20世纪80年代展开,这年代未免过于久远了。
其实对于80年代电影的研究来说,上海系导演得到的学术关注相对较少,这首先是地缘因素。另有一个原因则是上海电影在80年代所遭遇的名誉危机。上海电影制片厂(下文简称“上影厂”)标志性人物谢晋,在80年代中期首先被一些上海的年轻人所反对,之后几乎是学界整体性的批判。人们指责上海电影的整体“庸俗化”,因为上海电影创作在80年代未能如北方电影同行那样,发起巨大的探索电影新浪潮,这浪潮催生了北方第四代和第五代导演在电影形式方面的创造力。在80年代电影界无限的求新意志下,上海电影的艺术展现似乎过于保守了,它被视为旧上海电影体系余孽和好莱坞电影留在中国的大本营。
今天看这股舆论的倾向性,已然非常清楚,虽然后来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浩大的商业化时代,又重新肯定了上海电影路线,但上海电影地位江河日下,并在今天被边缘化。如果说上海电影曾是中国“早期电影”的同义词,如今中国电影文化的中心则迁移到了北京。而这一变化从80年代就已经有了铺垫,据杨远婴教授回忆,在80年代中后
期,黄蜀芹每到北京,都会向她抱怨——声音全部来自北方,上海已丧失声音。不过于今天来看,80年代的上海,黄蜀芹、史蜀君的上海,纵然有那样的失落感,但80年代仍然算是上海电影最后的黄金时代了。
以上关乎上海电影注意力分配的历史,算是讨论史蜀君等前辈的背景知识吧。关键仍然在于:如何理解史蜀君导演的电影创作?在既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已经将史蜀君导演置于中国电影导演第四代的文化谱系当中,他们从一代人的电影表现中找到了共同点:题材的一致性以及美学上的某种一致性。而“代”的研究是作者研究的替代,是一个默认作者主体性被贬低了的研究方法。我们勾勒和指认的仍然是一个群体性面貌,一个时代风云所塑造的共相,80年代的电影学者很少去发掘属于每个个体的独特性。
那独特性也许真的不在?或者纵然存在,也是稀薄的?或者是一种学术方法和知识模型的运用带来的结果?今天看80年代电影学术界的论述里面,很少见到个体主体性这个概念。当文学界大谈存在主义的时候,电影学术界在谈论结构主义。多年以后,80年代的理论闯将们在回顾那段历史时,非常自豪于他们比其他领域的学者更为先进,因为他们以结构主义方法替代了存在主义的论述。因此当第六代被当作中
国第一代独立电影人出现的时候,有些学者是非常悲观地加以否认的。也许他们认为被称为“中国独立电影开创者”的第六代仍然是一个被历史、被中西方意识形态对抗等体制性力量所深深作用后的产物,人们夸大了他们的创造力与自由。
在今天,我并未否定结构主义和意识形态批评等学术方法,它们针对80年代电影具有有效性与深刻性。但是若以中国社会的同心圆结构来解释一切,将一切差异抹平,若仅仅言说一代电影人的相似性,我们又如何去理解不同作者艺术成就的高低?如何看待每个人不同的美学倾向、题材偏好与电影情趣?80年代最为时髦的学术研究里面,很少去潜心勾勒单个电影人的身影与电影意义的关联,但将作者个性深度的可能性与作者经验的独特性纳入进来,我们才能看到一部电影得以成型的完整机缘。
如若不然,我们如何去纪念一位导演?尤其是一位在当年被认为有成就的导演?
如若不然,80年代还有什么值得纪念?
二
其实在针对第四代导演的学术论述里,史蜀君并非核心人物,她经常因为不符合某种代际研究的一致性而被搁置一边。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研究者对其美学没有产生高度认同,但也可能预示着她的某种不可归纳性。
史蜀君导演去世前的两年,我们曾有两次交往。最初我是为博
士论文收集材料,来到她在上海建国西路一栋花园洋房的家,她和丈夫严明邦住在其中的三层。房间宽敞,窗户镶嵌着富有宗教气息的彩绘玻璃,这是清末达官贵人接受西方影响后的装饰风格。我们谈到宗教的话题,史蜀君导演告诉我,她的家庭其实有基督教背景,她的母亲早年在西安上的是教会学校,母亲慈爱且有很好的生活情趣,这对她的审美产生了影响。
史蜀君的父亲于北大毕业,后来成为国民党的少将,家族里面有很多优秀人才,1949年后有亲属散落于美国和台湾,80年代方才恢复联系和往来。由此,她对于民国时期小康人家的生活以及后来海外资本主义的生活,都比别人有更多的了解。
史蜀君导演1939年出生于四川,所以名字里面有一“蜀”字,这名字来历与她的上影厂同事黄蜀芹类似——1937年年底国民党迁都重庆后,上海精英转移至国土之西南,大后方出生的孩子取名往往带有“蓉”“蜀”两字。这名字暗示着她不由自主的早期家庭历史。
“我来自于一个富裕的家庭。”她说。见识过繁华世相,所以当她在80年代拍摄琼瑶小说的时候,有一种亲近感。琼瑶小说多描绘资产阶级富丽的生活场景,80年代大陆尚且物质匮乏,道具师傅没有出过国,也不曾见识民国时期的富贵人家,为了营
造华丽的气氛,史蜀君将自家的花瓶、垫子等生活用品搬到片场使用,因此有人称她为“道具导演”。
史蜀君是80年代最早拍摄琼瑶剧的内地导演,是当时在大陆推广琼瑶作品最为得力的人。琼瑶夫妇都对她拍摄的电影相当满意。琼瑶也是来自大家族,与史导演年龄相仿,且同在四川出生。她第一次到内地来是为打版权官司,史蜀君第一部琼瑶剧《月朦胧、鸟朦胧》(1986)是在没有取得版权的情况下拍成的,琼瑶并未怪罪于史蜀君,而与她成为朋友,并在后来将《庭院深深》授权与她。如果说《月朦胧、鸟朦胧》里面的场景和人物情态还显得有些寒酸,那么到了《庭院深深》(1988)就好多了,电影无论叙事结构还是摄影和音乐,演员组织动作的流畅感与台词相当欧化的速度感,都给予当时内地观众愉快的观感。
史蜀君说,她拍摄《庭院深深》参照的是西方电影《简·爱》,而她所喜欢阅读的描写贵族生活的俄罗斯小说,也对她有所帮助。她曾向我讲述过她最为心仪的电影故事,那是她最终无法拍成的作曲家陈钢的故事:
“陈钢跟我讲了一个反右的题材,他爸爸陈歌辛是20世纪30年代有名的作曲家,劳改了,陈钢年轻不敢去看爸爸,后来他还忏悔自己当年的不敢去。他妈妈在一个风雪天赶到劳改营,走
了两天两夜,他爸爸拿了自己用套鞋接的雪水,用一个铝皮的类似军用壶的东西烧了点开水,拿出来不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的一点点咖啡,给陈钢的妈妈喝。这种知识分子,在劳改营里,会这样营造氛围,这是草根没有的,是独特的。这样的场景多好看!有点像十二月党人的家属在流放地的感觉。”
她对所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似有天然的亲近,通过上述描述,她的情趣、志向似乎使她的选材倾向和电影风格有了一个可以解释的来源。电影面貌不是完全被他者决定的,她自身至少是其发源地之一。当然,她的内在性必然不是其电影意义的全部来源,她的电影处于80年代意识形态氛围和国营制片厂系统里面,这一点她无法超越。
家庭出身在自我形成之前就已存在,在她拥有行动力量之前就已发生,它带来的文化力量为她所使用,也制约着她。这项因素究竟是促进了主体性或作者性,还是对于作者主体性的否定?我认为它们同时存在。从外部环境来说,其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的家族历史成为其个人事业的负累。史蜀君1964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被分配到武汉拍样板戏,拍摄过程中被人举报其“出身不好”,被安排去放映幻灯片字幕。后来她因为丈夫的关系调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她给谢晋当过场记,在给
舒适当副导演时表现出了一定的导演能力,但是她的出身仍然使她不具备做导演的资格。
史蜀君后来说:“徐桑楚厂长是有恩于我的,我在拍《女大学生宿舍》的时候,是1982年,厂里有人对我提出质疑,说史蜀君是什么出身!还有三个女党员跑到党委书记丁一那里告状,说她有美国台湾的亲戚,怎么可以拍电影!后来徐桑楚很生气:他妈的,我一个厂长用个导演的权力都没有吗?我一定要她拍!”
《女大学生宿舍》是厂长的命题,但史蜀君毕竟获得了做导演的机会,她创作时心态上如履薄冰。在拍摄过程当中仍然出现阻力,领导从北京派人调查本片状况,因为有人告状称它包含精神污染和自由主义倾向。“我听到后三天没睡,我很害怕影片被禁,我想起我影片中出现了连衣裙、牛仔裤,对于大学教授陈旧教法的批判……但后来领导看了样片,认定没有问题。”
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此片沿袭了80年代早期电影亢奋的表演风格和神情样貌,视觉上也同样有着当时电影的一般性缺陷,比如变焦镜头的滥用,但是它仍然具有独特的气息。这气息是什么呢?
导演听从朋友的建议,是按照青春片样式来拍摄这部电影的。在这一名义之下,电影加入了一些时尚元素,青春的面孔和服饰,集体舞、轻音乐,甚至让其中的人物说
出了相当锋利的台词:“只有自我,才是绝对!”这些零碎的话语和元素是拼贴着展现的,不是通篇有机的系统表达——事实上她也无法系统地以此去表达。但是对于当时的观众来说,这已经具有较强的刺激性。在这种个性的偶然展现以外,整部电影在意识形态上是顺从的,是符合当时的权力秩序的——比如对校长的误会和赞颂。
中国第四代导演作品存在男女分化的现象。男性导演多关注社会框架性议题:大的政治事件和主要社会矛盾,比如“文革”伤痕电影。第四代女性导演则多转向了家庭、社区、学校、儿童、情感等更小的社会角落,如《苗苗》(1980)、《泉水叮咚》(1982)、《夕照街》(1983)等,在这些作品中,“文革”等因素纵然出现,也多非前景中的存在。《女大学生宿舍》拍摄的是当代大学生活,但内里携带伤痕电影的思路。女主角匡亚兰内向、勤奋,有正义感,但是她过着相当窘迫的生活,原因则深植于“文革”当中。她的母亲揭发了丈夫,然后改嫁高官,导致了匡父的早逝和自己一贫如洗的大学生活。匡亚兰在表面上时常处于生活窘迫当中,但事实上有一个作家父亲和富裕的母亲,她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底层穷人。我想,这样的设计也许更能够让导演本人与这个角色产生认同吧。
像
“文革”反思电影往往也带着“文革”气息一样,本片也仍然具有“文革”时代的影子,或者说与“十七年”意识形态一致的部分,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继续滑行。《女大学生宿舍》设计了匡亚兰母女最终决裂的亲属关系,这和“文革”中家庭划分界限有一样的决绝的表情。有趣的是,电影在不时展示着“资产阶级趣味”的同时,又时刻显露着“工农兵至上”的意识形态。主角匡亚兰属于准无产者,没有任何家庭成员也没有任何收入,她在电影里面拥有着最高的政治正确性;而当室友辛甘迷恋上高年级同学兰为时,匡亚兰认为她的爱情过于幼稚,教训的理由是男方在做知青时就有了一个女友,那个女友至今仍然留在农村研究林业;而兰为在思考当下大学生与社会的关系时,讲到他在河西走廊遇到一位挑粪的农民,他认为自己的人生思考应该从这里开始……因此本片在意识形态层面是安全的。正如上面所言,它的出格和吸引人的地方是一些浮在表面的意象、片段,作者的策略乃是将多种意识形态元素杂糅在一起,使其具有多重的满足功能。本片热衷于展现湖光山色、旖旎风光,但它又不仅仅将大自然处理为业余休闲生活的场所,而将它同时展现为劳动场地。电影最后一个镜头,就是宿舍室友在
江边帮助贫困生匡亚兰一起推砖头的场景。
本片获得了1983年捷克卡罗维发利电影节处女作最佳导演奖,此奖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疏远了20年后,首次给予中国电影的奖项。这个奖项在中国显然具有国际政治的含义,它无疑为史蜀君导演在上影厂的创作地位进行了赋权。今天我们考察80年代最能获得电影作者资格的导演,会发现除个人才能外,尚有其他的因素发挥作用。创作空间的获得往往与个人家庭背景相关,80年代的美学革命者,比如谢飞、吴天明、米家山、杨延晋如此,第五代导演更是如此——陈凯歌和田壮壮,包括将电影《原野》(1981)直接送往威尼斯电影节的凌子……作为特权者的反抗者,他们的出现是80年代中国电影界的重要现象。那时候的中国电影大多远非平民电影,从各个角度来说都是如此。电影导演的独立性、作者性、主体性,只有在相对自主的创作空间中才更能获得。80年代的确有一批人因特殊的机缘获得了相对多的自由,这是在社会主义制片厂系统性力量之外,需要考察和了解的方面。对于史蜀君来说,她由此次得奖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创作空间,此后才有“惊世骇俗”的《失踪的女中学生》(1986)。
三
如果对一位交完毕生作业的导演进行归纳,可以用几个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