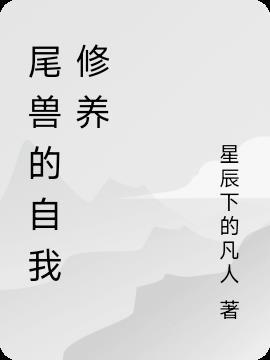风云小说>侍女的品格裴千羽 > 第11頁(第1页)
第11頁(第1页)
晴秋笑了,誰家裡沒有幾隻捨不得扔的破碗呢,她家也使不上這樣的好東西。
煥春抬眼,笑嘻嘻作揖:「多虧了你,好容易劉嬤嬤使喚我一回,還差點漏了怯。」
晴秋笑道:「這府里淘換下來的傢伙什,沒有一千樣也有八百樣,誰能記得牢我不過也是湊巧見過罷了。」
話這麼說,卻也把袖子一擼,示意煥春和她一起搭把手,抬起來。
煥春卻擺了擺手,跑到外頭喊了兩個小廝,四人合力,好歹把碗筐子抬進廚房門口。
劉嬤嬤趕將出來,拍著胸脯:「虧得叫你們找見了,不錯不錯,正好解了燃眉之急!」
煥春卻道:「虧得是晴秋記著。」
劉嬤嬤笑著揮揮手,打發她倆。
煥春還要往那門裡瞧兩眼鮮,晴秋惦記著灶上的熱水,扯著她走了。
她們不知道的是,這一來一回,都叫那菱花窗裡頭的一主一仆瞧得真亮的。
……
席面預備好,管家嬤嬤打發身邊人去後院請老太太並幾位太太。
其實大家都知道,這種不年不節,只有一幫泥腿子的宴會,這幾位是輕易不來的,這是當家老爺穆三爺,和當家姨奶奶張書染的場子。
果然,沒到一炷香的功夫,便回來傳話:「老太太才剛吃了幾盅酒,正釅著,不好下地,說不來了,叫姨奶奶好生招待著,另賞了十緡錢,算作彩頭;大太太伺候老太太,自然也是來不了,賞了五緡;二太太原想來的,不成想頭晌吹了風,現下正犯頭疼症呢,只好告假,賞了兩壇碎金酒,以作助興。」
書染起身,命紅玉接下獎賞之物,道:「老太太和太太們身子都不爽利,委實不該過分叨擾。這些錢酒俱是她們的慈心,合該分賞下去,大家受用。」
說罷,也叫紅玉拿出五緡錢來,連賞賜的一起,每人都賞了一把錢,一盅酒。又命人搛了幾碗軟爛葷香的菜餚,送到老太太和兩位太太處,搛了兩碗素食,送到三太太處,表作孝心。
一番事畢,宴席終開。
東廂那邊自有二老爺三老爺招待,籌令划拳,熱鬧非凡;下人房這頭張書染坐鎮,也是笑逐顏開,杯籌交錯。
這會子需要端茶遞水的小丫頭就多了,管家嬤嬤叫劉嬤嬤也挑幾個伶俐的過來打支應,晴秋紫燕煥春等幾個便洗手過來伺候。
*
這種在主子跟前露臉的活計遠比做粗活難應付得多,晴秋等幾個小丫頭端著茶盤一步不敢亂走,一眼不敢亂看,魚貫著次序,排桌斟敬。
因都是僕婦嬤嬤們的會餐,況且又是擺在下人房,席上眾人越發沒了拘束,行令喝酒的,起鬨逗的,論起喧鬧來也不賽及東廂的爺們。
趁著錯步回身時,紫燕悄悄沖晴秋遞了個眼色,晴秋輕輕回頭,只見那席上,先前才吃了瓜落兒的李氏正捧著一壺酒湊到頭桌,矮身哈腰地往管家姨奶奶跟前說著什麼,一張老臉笑得朵花兒似的。
晴秋留神那幾個管事的的態度,果然無不與她說笑,不禁心裡一冷,想劉嬤嬤的話果然不錯。
抽身之際,視線卻不免被一抹婉約倩影吸引——
*
坐在主位上的管家姨奶奶約莫二十七八歲年紀,鵝蛋臉面,瘦削身量,一頭烏髮松松挽著一個髻兒,任誰打眼一瞧,都曉得她不是本地生人,渾身自有一股難掩的裊裊水鄉風情。
她穿一身剪裁合宜的雀頭青緞面長襖,茶白褶裙,外罩珊瑚紅比甲,被一圈人哄著敬酒。
吃了兩盅擺擺手,大約是醉了,此刻正有些懶怠怠地倚在玫瑰圈椅里,袖口滑落,露出一截細瘦的腕子,以及腕上兩隻絞絲銀鐲子。
車把頭老婆李氏殷勤地矮身過來,堆笑開口:「姨奶奶您嘗過千金萬金的酒,也嘗一口我們自家釀的,埋在桃花樹底下足有十五年,前兒二太太打發人來要,都沒捨得開瓮呢!」
張書染轉過頭,未語先笑,推拒道:「我就是一杯的量,才叫她們哄著吃了兩盅,已經不成事了,恐怕無福消受你這十五年的陳釀。」
李氏又哪裡肯放棄,只笑道:「不礙的,姨奶奶若喝不了,我斟一杯您好歹聞一聞香氣,也是這酒的造化了。」
說著,果真斟了一滿杯,捧至張書染面前。
張書染不自覺地輕皺了下眉毛,最後還是抬手拂了拂,細嗅之下果然酒香撲鼻。撂開手,笑道:「確乎是陳釀女兒紅,聞之便甜蜜馥郁。」因問她:「你女兒,我記得叫採蓮,老太太屋裡的,今年幾歲想來這酒是為她預備的。」
「十五啦,姨奶奶料得不錯,這原是替她預備下的陪送,就等她放出去那一天呢!」
「既如此,嬤嬤很不該將這酒取出開瓮,再埋個三兩年,等丫頭出嫁了,不管是自飲還是拿出來賣,都不是眼下這個味道、這個價錢。嬤嬤你虛長這許多歲,焉不知這世上還有『長算遠略』的道理」
這話即像是說酒,又像是說別的,一時那李氏的笑臉僵了一僵,在旁眾人皆是抱著臂膀輕笑。
不過姨奶奶說話一向愛咬文嚼字,有時大伙兒聽不大懂,便只會頻頻點頭附會明白,顯然李嬤嬤也深諳此道,連忙應了個是,只把尷尬與嘀咕藏在心口。
這一來一往也只發生在主桌,旁人是聽不見的,晴秋等小丫頭們再斟過一遍茶水,皆肅穆退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