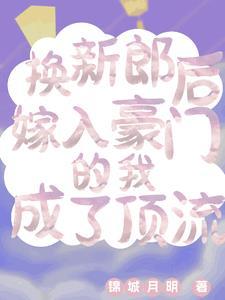风云小说>穿越医术精湛的 > 第49章 踊跃报名(第2页)
第49章 踊跃报名(第2页)
他朝温云昔笑笑,站到了曈云右边,神情平静。
石惊是第二个上台的,他瞪了岩山一眼,跑到曈云左边站定。
曈云皱眉,“你上来干什么,下去!”
石惊被曈云眼神看得下意识后退两步,察觉自己胆怯后,又梗着脖子道:“我怎么就不能去了?!我就要去!”
曈云哼了声,懒得管他。
可是他自己要去的,死了残了,可怪不得她!
台上很快就站了五十人,未抢到名额的少年们纷纷懊恼惋惜。
早知道该站近些。
温云昔数了数,女孩二十八人,男孩二十二人。
这晚,五十三人整装待。
曈扎带着族人们为他们送行,拉着人仔细叮嘱。
勿骄勿躁,听曈云指挥。
最后,又将女儿带到旁边足足说了一刻钟。
女儿哪里都好,就是太倔强。
他总有些不安。
于此同时,县衙大门被砸开,喊声四起。
煅知县大怒:“弋红飞,带着他们滚!”
“走可以,先把他们的板子打了。”
弋婶子手里拽着根麻绳,绳子那头栓了一长串。
益生堂二十六人,整整齐齐地捆在一起。
狼狈不堪。
煅知县深吸口气,早知道就不干这知县了。
憋得慌!
桑族长没离开前,他们怎么不敢闹事?
就看他好欺负是不是?!
“来人,将他们都给我打出去!”
弋婶子神情一冷,撩起袖子就准备开打。
跟着她来的那些人,倒是有不少吓得往后退。
毕竟是县衙,煅家也不是好惹的。
他们可不是弋红飞,有红月军的背景。
眼看就要打起来,三个老人被家中小辈扶了进来。
“红飞,石曲,别伤了和气嘛。”
水爷笑着上前,慢悠悠地站到两人中间。
煅知县脸色好了些许,他后退两步,态度带了几分恭敬。
“水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