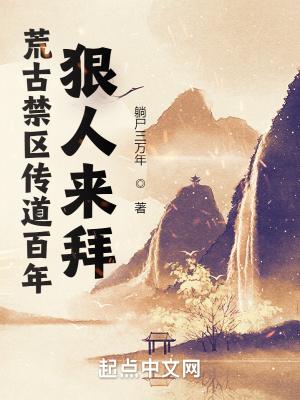风云小说>童养夫晋江 > 宫廷政变11(第1页)
宫廷政变11(第1页)
[]
她慢慢坐回了栏上,神色淡淡,也不叫停,就看着曹庄头哭。
人一直哭很耗费心力的,而且还是假哭,更是耗费许多的精神,照着他这好像奔丧样的劲头和架势,苦累到头痛不消太久。
对付老油条,这种软钉子先让他难受难受,让自己畅快畅快很不错。
曹庄头哪里料到谢妙旋变脸好像翻书,猛作,猛收回。他哭了好一阵子,都不见她有一点动静,像是压根没有开口的打算,心中不免有些奇怪,每次他跟贵人哭诉,要么是不耐烦将他打走,要么就是同情泛滥,甚至有给他赏银的。
便悄悄打开指缝,就见女郎神色严肃盯着自己看,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他眼珠子一转,便连忙又继续放声大哭。
又过了好一会儿,他感觉自己哭到喉咙干,眼睛涩,太阳穴也开始突突跳。
实在是有些哭不下去了,便装作抽噎着停了下来。
谢妙旋看他哭得两眼布满红血丝,深觉欣慰,“曹庄头孝感动。。。咳感人,这样吧,你回去把这些年的账簿拿来我瞧瞧。”
“这。。。。。”曹庄头表情都空白了一下,这,怎么跟他想的不一样啊,女郎也没有过来扶他一下,还一脸的兴味?!是他眼花了吗。
“怎么?”
谢妙旋叹息一声,“要是你连账簿都不敢拿来我瞧,我又怎么相信你是真的不呢,差点我就信了呢,看来你莫不是欺上瞒下,克扣庄园农户,中饱私囊了,要是这样,这种人我可是留不得的。”
大牛半侧步,刷一下抽出腰间佩刀,寒芒一闪而过。
曹庄头连忙爬起来,“不敢不敢,我这就去拿,这就去拿。”
他倒退着出去了,三步并作两步回到家中。
屋里曹氏正小心用文刀裁纸,侧抬头看儿子写好了一张大字,笑的见牙不见眼,“我家坚儿出息了,今又学会了一个大字,等下你爹回来了给他看。”
说着又珍惜摸了摸桌案那本书,“你可要好好学,这可是你堂表叔得了县令赏赐的,娘磨了好久他才同意拿来给你临摹,等你学会了一千字,娘就让你爹出钱给你买个一官半职做。”
院门突然被人大力推开,案几上的年轻男子抬起头来,喊了一声,“娘,你手拿开。”
神情倒是老实巴交的,甚至有些愣愣。
曹氏听到声音心中一跳,道,“坚儿莫怕,你继续写啊,娘出去看看,是不是那小贱蹄子又闹起来了,看我不打死她。”
她操起门边的扫帚,插着腰走出去,定睛一看竟是自家当家的,连忙放下扫帚随手在腰间围裙拍了拍。
走近一看,见他眼睛红肿,像是被人打了两拳,惊叫一声,“老头子这是怎么了,可是那今晨在门口大喊大叫的野蛮子打你了?!”
“我早就叫你躺在床上装病就好,不用理他,只要你不出去,我去替你着,他还能将你从床上拉起来不成!这来的不过是一个女郎,又不是郎主,能懂得什么,还召见…哼,管得恁宽,你作为这京郊最大庄园的庄头二十多年,她就是找你来耍耍世家贵女的威风。”
她埋怨个不停,“那些个庄户早被我们警告过了,不敢同她说话的,她在这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看她待不了两日鲜劲过了就要走的,你就随便应付应付就好了,竟然打你?!”
曹庄头头也不回,不搭理她连珠炮似的话茬,到厨房拿了水瓢咕咕咕给自己灌了一肚子,才觉得火辣的喉咙舒服了点。
转步往里屋去,曹氏还要跟在他身后絮叨,好容降下去的那把火,哗啦一下又升起来,“够了,我头痛得很,先去睡会儿,午食你再叫我起来,还有将放在坚儿书房的账簿,找出近两年的给我备好,我下午有用。”
他眼底阴狠一闪而过,心中想着账目早就由他县衙做主簿的侄儿做好了的,根本不惧查账。
但他偏不想立时就给谢妙旋送过去,好歹拖上她一拖,这些贵人往日惯赏风弄月,都不是好耐心的,兴许过不了一时半会儿,她就忘记这事了。
这乡下庄园又哪里有京都繁华,他也不觉得谢妙旋会常住在庄园里,自觉只要向上敷衍做戏到位就行。
现在他正不舒服着呢,大清早就被那野蛮子吵醒,这会儿又头痛得很,打算睡个回笼觉再去应付这位贵人,倒头睡了过去,根本没有心情听曹氏夸耀宝贝儿子又学会了一个大字。
曹庄头一走,大牛就想跟着去,“女郎,这老叟不老实,办事拖沓,不如我去跟着他催他快点。”
谢妙旋制止了他,他的脸色肉眼可见委顿了下去,喜怒哀乐都在脸上,鲜活得让人看了失笑,一脸苦大仇深。
“不急,欲让其亡,先令其狂。走!带上我们的人,随我去庄园巡视一番。”
京都最大青楼。
绮陌春坊大堂人声鼎沸,莺歌燕舞,到了三楼则是杂音尽消。
静谧包厢房内。
谢元驹缓缓放下茶杯,细长的指节在桌面规律敲击。
“三日前谏议大臣文征被现死于家中,死因不详,浑身上下找不到一点外伤,是觞叟仔细查验过后现他乃是被人一剑封喉。这动手之人刀法可称当世宗师,伤口隐于肌理之下,寻常人根本察觉不了。”
阙思单膝跪,禀告完了仍旧一丝不苟跪着,并不敢抬头看眼前人,眼神盯着眼前砖,仿佛上有朵花吸引了他全部心神。
一道洪亮声音插入,有些戏谑味道,“阙思,你怎么还是老样子,要是主公不开口,你是不是就跪死在这里,若是让别人知道堂堂暗隐第一人竟然是这么个死法,怕是能惊掉下巴。”
谢元驹,“没听到觞叟所言么,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