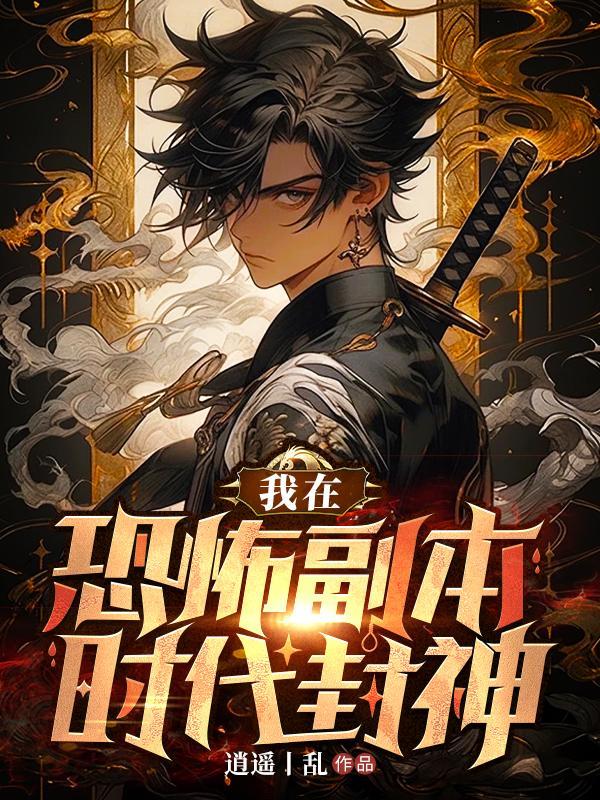风云小说>休假进入逃生游戏 > 第22頁(第1页)
第22頁(第1页)
「咳咳……我沒事,我跟著好歹能有個照應。」
阿墨倔強地伸出手,沒人接,祁亞趕緊又把他扛過來。
他倚在祁亞肩頭,小聲道歉:「對不起,讓你看笑話了。其實我挺有用的,真要遇到危險,你把我丟出去還能拖延時間。」
「胡說八道什麼。」祁亞罵他:「遊戲還沒失敗呢就想亡羊補牢了?真是笑死我了,我要靠你來給我拖延時間?」
「我要能逗你笑也挺好的。」
因為祁亞扛著阿墨走得很慢,兩人漸漸落了隊,上樓梯時格外吃力。
阿墨低聲說:「這遊戲太血腥太殘酷了,呆久了人也變了,都不會笑了。」
在這種高強度的死生離別面前,人的確會成為一個沒有感情的殺戮機器。
祁亞搖了搖頭,示意阿墨看兩側的畫:「那你不如放平心態,找找別的味。」
例如她這個休閒玩家,還有空看古堡的油畫。
一幅幅油光褪盡的人物肖像都是精品,完全值得收藏在羅浮宮,現實世界裡只能隔在三米外觀賞。
現在她甚至能近距離看,右下角的簽名都看得一清二楚。
『勞里公爵二世。』『可蘭侯爵夫人』『愛德華七世』……
越往上,年份越近。
最後一幅畫落款兩百年前,郎曼男爵。
「男爵是最低吧?看來城堡也落魄了。」阿墨苦笑說:「會不會是把錢都用在藏品上了?」
「一路走來,爵位有高有低,發色不同,顯然不是城堡主人的繼承順序。就是一些藝術家的名作。」祁亞對自己的歷史常識還是有自信的。
爵位反覆橫跳就很不正常了,更不提一代代人毫無相似,總不能是這個家族有綠帽子傳統?
「可他們都拿著那柄權杖。」
阿墨小聲說:「權杖上都有那個蛇形圖標。」
一心走樓梯的祁亞立刻轉頭,正對上郎曼伯爵的肖像畫。
畫上的男子意氣風發,而手中的權杖猶若一條邪惡鬼魅的蛇。不正是城堡主人剛剛毆打安琪的那一根?
不死研究,鮮血,蛇。
小鎮即將舉行的祭典,象徵邪惡的兔子,人皮書與巫術。
眼前這幅郎曼男爵不正是現在那位白髮蒼蒼的男子!
「完了,如果是巫術,鑰匙就是一個障眼法!安琪偷鑰匙只會自尋死路!」祁亞快分析:「還記得書房大門嗎!根本沒用鑰匙就開了!」
安琪這個npc的作用到底是什麼?
祁亞頭疼至極,千千一臉驚恐地沖她跑過來。
「安琪沒法用!我們的推理是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