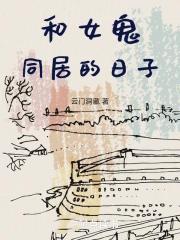风云小说>白昼已逝 > 第1章(第3页)
第1章(第3页)
但我错了。
死亡之梦就这么开始了。
四周一片漆黑,喉咙干的像被人强行塞满了刀片,前所未有的饥饿感几乎能瞬间将人逼疯,但我只能嗅到自己脏腑深处散的血腥气。鼻腔也是干燥的,还混杂着沙土特有的粗糙颗粒感。
我似乎被掩埋在一座废墟中。
忽然,有人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
他说:“我们已经一起被困在这里四天了,救援队不知何时会来,若是两个人一起饿死,实在没有必要,不如牺牲一人,换取另一人活命。”
“只能活一人,认命吧。”男人低声道。
我听到了“哧喇”一声,那是锋利金属出鞘的声音。雪亮的锋刃划破黑暗,隐约照亮了他清冽的眸光。
即使知道自己死到临头,我也不得不说,那可真是一双漂亮的眼睛。
一连七晚,我重复做着这同一个梦我和一个男人被一起被困,我不良于行,而他抽出了利刃,看上去想宰了我当储备粮,好等到救援。
这段重复的梦掐头去尾,既没有前因,也没有向后延续不过,或许我应该感到庆幸,因为梦境无比真实,能逼疯人的痛楚和干渴都货真价实。
而且合理推测,如果梦继续下去,下一步这人恐怕就得捅死我。
哦,不对,如果是要将我作为粮食,他便不能立刻杀了我,而应该割破我的静脉,让我的血缓慢流出,缓慢凌迟我,让我一点点感觉自己的生命流逝,成为一具干瘪的皮囊。
虽然始终没有更多新的信息,但好在随着梦境的重复,我注意到了更多的细节。
第二晚,梦中,我注意到他拿利刃时用的是左手。人们在生死对决时自然会使用自己的惯用手,因此,我推测他是个左撇子。
第三晚,梦中,我终于习惯了这具废墟中的破烂身体,能调动五感查探周围。
依然一片漆黑,但我意识到那男人的一些用词和语气也让我觉得熟悉。
于是,醒来后,我将梦中他说过的那几句话默在我的软面抄上。
我少年时不学无术,曾粗浅涉猎过一些语言学通识。知道怎么通过Ipa、嗓音停顿符号之类的手法记录一段话的语气和停顿变化,这让我能够精准复刻下梦中最重要的信息也就是男人的言语细节。并在白天的时间里不断斟酌和回想。
接下来的三晚,我已经摆脱了最初的痛苦和恐惧,不断通过梦里的细节完善关于男人话语的记录。而这时,那种古怪的熟悉感也越来越强虽然我看不到男人的脸,但我有种直觉:
我认识他,或者说,我“曾”认识他。
第六日,临近国庆,大学图书馆闭馆两日,其他时间换班轮值。
于是,在白天我也有了更多时间。我开始像查阅书架上的书籍一样翻找我的记忆,确认这男人到底是什么人。
我圈选了一些范围,但是这帮助不大。
我的头颈部曾受过重伤,这让我虽不至于完全失忆,但常有模糊,情绪和过往对我来说,常如雾里看花。只是我从来不当回事,觉得现在活得痛快就行了,如今却成了一桩阻碍。
其实,隔壁奶奶的房间柜子里满满放着贺白从小到大所有相册、成绩单、奖状。
但我知道,这些东西对我不会有任何帮助。
第七日晚,我最后一次重复这个梦。
梦还是一模一样,只是这些天下来,我已经对男人的台词熟的倒背如流,因此有些走神。而这让我反而听到了另一个先前被忽略的声音。
那像是从远处传来了若有似无的钢琴乐声,我屏息凝神听了一会,正好是一段重复的段落……
我竟然立刻想到了这是什么曲子。
中文译名是《晨曲》,是挪威作曲家grieg的著名作品,足够悦人欢快,适合做庆典背景乐,但在我国到底不算脍炙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