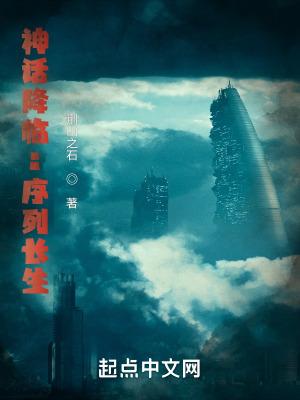风云小说>老城街小面 > 第350章(第1页)
第350章(第1页)
“天光乍亮便走了。”唐二浑不在意道,“端午休沐只得一日,他前脚从娘子房里出来,后脚就唤砚书套车往书院赶,连朝食都未用哩。”
哦,刚走的……沈渺颔首至半,忽地僵住:“你说什么?”
“我说九哥儿一早就走了啊。”
“不是不是,你从头再把刚刚的话说一遍。”
唐二不理解为什么同样的话非要说三遍,但还是一字一句地讷讷重复道:“我说九哥儿一早从娘子屋子里出来便……”
“好,停住,不必说了。”沈渺不由扶住了一旁的柱子,脚步更加虚浮地往洗漱的水池边走去,心里都尖叫出声了。
九哥儿…从她屋子…里出来……
她昨日干什么了她?沈渺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九哥儿这样守礼得连“轻薄”都要征求得她同意才会亲下来的人,是绝不会擅入女子闺房的,他一定是被她强迫的!
要命!当真醉成浪荡子了!
还把人吓得连朝食都顾不上,带上砚书直接趁天没亮便逃了去……沈渺掬起一捧凉水泼面,放了一夜的井水冰凉,她被刺激得脑中清明了一瞬,忽地记起些零碎光景——自己搂着九郎脖颈倒在他怀里,踩着满地月华被横抱着回房,末了竟捧着他脸说些浑话……
要死要死!她全想起来了!
沈渺深吸了一口气,她果然做了不得了的事。
绞着帕子拭面时,沈渺擦脸的手又顿住了,等等……但后来她真睡着了,九哥儿不会真就这样让她抱着胳膊守了一晚上吧?
她回屋换好衣裳,深刻地检讨了自己,怎么能犯经验主义的教训呢?真不该小瞧古代的酒的。这回好了,丢脸丢大了。
并发誓以后再也不贪杯了。
家里如今一堆酒鬼,沈渺进灶房时,福兴已经在熬鸡汤小米粥了,鸡架子炖得高汤单独撇了油,便往洗好的小米里倒,放在灶上咕嘟两刻钟左右,加些盐,撕些鸡肉丝拌进去,再小火咕嘟一刻钟,便能吃了。
这样的粥宿醉之人喝最好了,养胃滋补,香香暖暖。
沈渺捧着粥,坐在廊子下唉声叹气地喝着。济哥儿这才像屁股着了火似的从屋里冲出来,飞快地抹了牙粉,使劲儿刷起牙来,急得不行:“完了完了,今儿书院还有早课,睡过头了!”
吃了两口粥,沈渺又看着济哥儿在眼前跑来跑去,一会儿去院子里拿晾的衣裳,一会儿又跑回屋里穿,没一会儿又从屋里冲出来,去灶房收拾这个月的干粮。
不一会儿,唐二跟着慌忙跑出来,帮他套好驴车,嘴里念叨着“不慌不慌,肯定能赶上早课”,可自己却比济哥儿还着急,跳上车辕,鞭子一甩,就送他去书院了。
两人一驴风风火火地冲出了巷子。
沈渺又叹了口气,撑着下巴回想起昨夜的事儿。
原来她夜里抱的不是前世她喜欢的长条猫咪抱枕,而是九哥儿的胳膊呀。想到自己抱着人家胳膊当猫枕蹭,还叫谢祁误以为她吃了酒面上起疹痒痒,用指腹替她揉了整宿……
啊,沈渺无声地揪住鬓发,想找个地洞钻。
就在沈渺内心崩溃的时候,院门口探进来一个簪花的大脑袋,药罗葛笑眯眯地打招呼:“沈娘子早哇,吃早饭呢?”
沈渺松开手,放下粥碗,恢复平常的样子,起身去迎:“咋来这么早,吃早饭了没?要不要来碗粥暖暖肚子?”
“吃了吃了,其实不早了!沈娘子甭忙活,乐江侯夫人催得紧,咱们现就往衙门结契去?”
沈渺也猜到了他的来意,就跟着药罗葛去了衙门。没一会儿就啪嗒盖了个大红印,沈渺捧着热乎乎、墨迹都没干的官契出来了,阳光正好照在她和药罗葛身上。
药罗葛美滋滋地揣着另一份要放在牙行备份的白契书,把钥匙递给沈渺,不住地躬身恭喜沈渺,之后就借口有事,急匆匆走了。
沈渺这会儿没啥别的事儿,捏着手里钥匙,决定走去原本是康记的临河铺子看看,也好琢磨日后咋改造。
过了桥,看着暮春夏初河岸边又茂密得像青纱帐似的篙草,她忽而想起去年观莲节和九哥儿站在桥上一起看烟火的日子。
那时候她还没弄明白自己心意呢,没想到如今都快和九哥儿成家了。
日子过得可真快啊。
想着那些令人心头温软的往事,她因自己昨夜做出的荒诞行径而感到惭愧的心终究慢慢平复了下来。
没法子,好的坏的,都是她嘛。
她忽然又高兴起来。
走到康记时这股子莫名的兴奋之情都还没褪去。
她再次仰头去看,这铺子上的匾额已经摘下来了,如今便不能再叫它康记了。
打开沉重的大锁推门进去,里头到是还算整洁,桌椅板凳之类的东西全都搬空了,铺子里空空的,积了一层薄薄的尘。
她又踩着咯吱响的老旧木质楼梯上了二楼,楼上两边用住竹栅栏隔出了六间雅阁,中间还有一大片空地可以摆放桌子,真是很宽敞。
走到露台上,视野更是开阔,河面上清凉的风扑面而来,能望见两岸拥挤的商铺和翻飞的招子,还有河面上时而经过的画舫、渔船。
露台约莫有四人宽,修了木质栏杆,日后倒是可以沿着栏杆摆一溜二人小桌,挂一串过街灯,夜里吹着江风喝着小酒,望着万家灯火闪烁,再听听小曲……想来很有氛围。
可这二层的临河铺子,到底该做何营生呢?
沈渺站在那儿沉浸地想了很久,从大城市里的酒店自助餐综合体想到了粤式茶楼……最后对比下来,可能还是觉得粤式早茶风格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