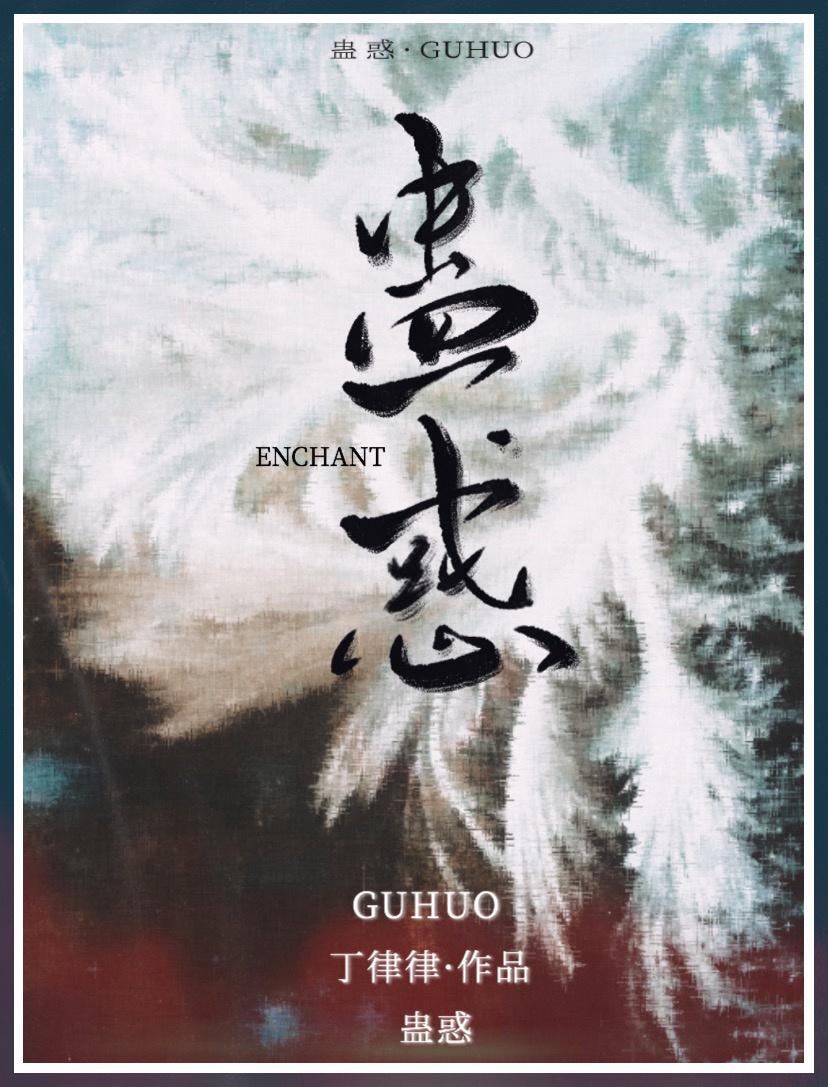风云小说>空间之末世养夫郎主攻还是受 > 第3章(第1页)
第3章(第1页)
「老爷们可是养小妾的,咱们仪哥儿长的这样好颜色,送进去怎麽不拿个百两银子的彩礼。」
「百两银子。」
王家二老同时惊唿出生,没想到这个小杂种这麽值钱,他们姑娘出嫁令初雪才给了二十两的银子添嫁妆。
王二郎翘起二郎腿,晃悠悠一脸高深莫测的说:「至少一百两,所以你们最近好好把仪哥儿养一养,体面些,打也别忘脸上招唿,咱们仪哥儿的那张脸值钱呐。」
王家二老也不是傻子自然明白这个道理,王老妪心中不顺但想到这个贱人都换那麽多银子,也就不闹腾了。
仪哥儿难得安安静静的睡了一觉,眼睛都睁不开,但浑身都在发疼。
仪哥儿闭着眼睛,乾瘦的手指摸着自己胳膊上的伤口。
稍微一动就疼的眼泪直冒,背上是伤口的重灾区,偏生仪哥儿被平躺着放在床上,无论是照顾的人还是医生没有一个人发生这件不合理的事情。
忍受着身上的疼痛,仪哥儿泪眼朦胧的看着屋顶,却也不敢大声的哭,怕声音吸引来人,又招来一顿毒打。
发烧烧的仪哥儿头都晕了,但是却烧不去肚子里的饥饿感,平躺在床上的仪哥儿肚子都是下陷的。
白天为什挨打呢,对了,是他实在饿得受不了,干完活躲在厨房里偷吃了一块干硬的窝头。
被来厨房找鸡蛋吃的金宝看到,後来怎麽了呢,是金宝吼叫着引来爷爷奶奶,他就被打了,再醒了就是躺在床上,屋外天都黑了。
仪哥儿摸着乾瘪的肚子,脑子里一直想着那块窝头,他还有一半没吃完,被金宝扔到地上踩成了渣渣。
仪哥儿悲哀的想,要是他吃快点儿,把那块窝头都吃了,是不是现在就不会饿了。
饥饿太难受了,比打在身上的藤条都疼,都难以忍受。
仪哥儿想起来喝些水压下肚子里的饥饿感,可是只是有这个念头,稍微一动身体,浑身的疼痛就让他明白,起身这件事对他而言就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连动都动不了。
倒在床上的仪哥儿难得有时间看看这件属於他的屋子,这是唯一还属於他的东西。
王大朗家的宅子盖的宽敞,一人一间都有富裕。
最初为了不那麽难看,仪哥儿的屋子没有被抢走,但屋子里面的家居摆设,衣服饰品,甚至是厚些的床褥都消失的乾乾净净。
还好现在是夏季,单薄的被褥也没那麽难熬,仪哥儿迷迷煳煳的微蜷缩着抱住自己,昏昏沉沉的在两位爹爹帮自己布置好的房间里睡去。
只是不知道梦里梦到了什麽,委委屈屈,害怕却又带着些开心的喊着:爹爹,小爹爹,小爹爹。
或许只有梦里的这一点时刻才能让仪哥儿真正的安心和开心。
第二天,睡到日上三竿的王二郎借着给仪哥儿相看的名头继续出去鬼混。
王老妪不想干活,就把二儿媳妇喊出来干活。
二儿媳妇昨日忙着地里的活儿,今天还要帮一家子老小做饭,甚至是帮仪哥儿煎药。
以往有仪哥儿这个更苦的做对比,二儿媳还没什麽感觉,今天看仪哥儿也不觉得可怜了,就觉得仪哥儿真的是婆母说的那样,一个小杂种,长的一副骚狐狸的样子,还要人伺候,又没有死在床上。真是晦气。
只不过当家的说这小杂种值钱,那就养养吧,他们卖猪都知道洗涮乾净,这给城里老爷的,怎麽都要头脸好看一些。
王二郎熟门熟路的摸到镇里最大的花楼,万花楼。
王二郎有钱也只能在这里点个便宜的姑娘,但就是这最次的也比家里那个黄脸婆好一万倍,有一次啊王二郎看到万花楼的头牌,怎麽说他们家的仪哥儿不比头牌差多少。
王二郎和万花楼的小厮打问过头牌的事儿,那个小厮的眼神王二郎至今都记得清清楚楚,那种不懈的看穷鬼看垃圾的眼神,让王二郎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
「咱们得头牌玉兰姑娘,场一首曲子都要单日消费达到五十两才能听到,不知道爷打算花多少钱请我们玉兰姑娘唱一曲。」
王二郎第一次见识到有钱人的世界,之前满是愤懑,但在昨晚看到仪哥儿後就彻底消除了。
什麽头牌,自家的大嫂和仪哥儿的长相可是丝毫不差的。
想到头牌唱一首曲就要五十两,王二郎已经看到白花花的银子源源不断的往他兜里来。
「白天不接客。」
王二郎被守门的拦住也不生气,一脸谄媚的说:「大哥我找红妈妈,我送人。」
「你」,守门的上下看了一眼王二郎,这年头卖小哥儿卖女儿的不少,他们这里尤其多,就是王二郎这个样子,守门的实在想不到他的孩子能好看到哪里去。
「我们不是什麽人都收的。」
「我知道我知道,不是我的孩子,是我大哥的小哥儿,很好看的,巴掌脸杏仁眼,不比玉兰姑娘差,当初他小爹可是大美人的。」
听到王二郎的话,守门的一脸鄙夷,卖大哥的儿子,觊觎大嫂,还是花楼的常客,这种废物要是他兄弟直接打死。
「行,你最好别骗人,我去说一声。」
红妈妈听完後,摆摆手说让门卫走一趟,看看货先。
路上,王二郎谄媚的问:「当初玉兰姑娘卖身钱是多少。」
白天本事门卫偷懒睡觉的时间,被赶来做这不赚钱的苦活,本就心里不爽看王二郎还一脸的自信,心里更是烦懒得搭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