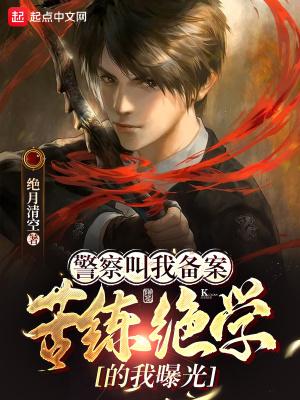风云小说>红楼之违和黛玉 > 第20章(第1页)
第20章(第1页)
唱罢,执事者奉酒、修案置于斐玉面前。
“师之道,大矣哉,今有斐玉情愿拜于尊师穆寻门下,承蒙先生允纳,愿执弟子之礼,秉承师训,团结同道,矢志不懈,没齿不忘,愿终身追随杖履,以求奉报先生殷殷之谊。”
斐玉跪于蒲团之上,敛容屏气,怡声下气,俯首拜讫。
穆寻接过执事递来的束修,抚须微笑,满意点头,道:“可也。”
“善哉!”执事道:“请行大礼!”
斐玉起身,拱手稽拜,额垂至席,九叩首拜至圣先师孔子神位,然后退后再前,再三叩,以拜先生。
“今你拜我门下,且记四点,为学应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修身当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此四点也,汝能乎?”
穆寻双目炯炯,朗声问道。
“吾定当不负先生厚望!”
“大善!即此,礼成!”
观礼的学子们看着少年礼成起身,又与穆寻身后一众老师拜见,皆沉默不语,不发一言,便是有那些原本心存不满的,也不敢在这种场面下狂妄出声。
直到穆寻含笑抚须带着斐玉与众位教谕相见,大伙儿才慢慢的有所动作,低声交流起来。
“听说昨日冯演带人堵他,反而被好好教训了一通。”
“今日一看,他小小年纪,居然也气度不菲。”
“不错,我这么小的时候,怕是比不过的。”
“山长大人愿意收他为徒,一定是有他老人家的道理,礼成事必,已成定局啦,你我就不要妄想了!”
众人暗暗议论,忽然此时人群裂开,一人穿出重围,高声笑道:“抱歉抱歉,我来晚了!还请师弟莫要怪罪!”
斐玉听到声音,与穆寻一同看向人群,只见一风流倜傥,英俊潇洒的锦衣男子疾步走来。
他眉如墨画,目若秋波,青丝以玉簪半束,散落下的发丝随风而动,更奇的是他腰上挂了一串儿的玉珏配坠、香囊络子,色彩缤纷,叮叮作响。
见到此人,原本还满面红光,兴致极佳的穆寻忽然面色一变,低喝出声:“行简!”
原来这人就是他的五师兄萧行简,可他的形象却与斐玉想象中的出入很大,他还以为自己这位师兄是个温和儒雅,潜心问学的人物。
可现在看来,“多情风流,富贵公子”用来形容萧行简却再也恰当不过了,这给斐玉带来了极大的维和之感。
“师尊您近日里可还好?”萧行简仿佛没有察觉穆寻的不满,他笑着向穆寻行礼,随后目光灼灼地盯着斐玉瞧,忽而笑道:
“这个小师弟好眼熟,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斐玉一怔,看向老师穆寻。
穆寻脸色不佳,方才还充满慈爱地一双眼睛变得极为犀利。
斐玉不由回忆起初见穆寻时,他欲叫五徒弟萧行简来与自己见面认识,却被仆从告知对方下山办事去了,找不到人。
那个时候,穆寻面色平静的淡淡道:
“他若事了,自会回来。”
那时斐玉就隐隐察觉了穆寻平静表面之下的不快与无奈,现在看来,萧行简虽然回来了,也没让穆寻开颜。
斐玉记得书院里的规矩有这么一条,如果请假,必须向书院监院和斋舍监督报备,准假给牌了才行,而且请假外出的时间不能超过半天,经常请假、越期不归、假满不回都会被书院开除出去。
这么一看,近三个月里萧行简都下山七回了,也没告诉山长穆寻,现在堂而皇之的冒出来,穆寻能不生气吗?
也不知道这对师徒间到底有什么故事,斐玉暗道,如今拜师礼成,他已经是穆寻的徒弟,萧行简的师弟了,但凡有什么事儿,他也必须力所能及的帮衬。
只是此时斐玉不好多嘴,老老实实的对萧行简躬身行礼,道:“斐玉拜见师兄,初次见面,失礼之处,还望师兄海涵。”
“哎,师弟太客气了,你别怪我太忙,连这等大事都迟到一步,师兄心满意足了。”
萧行简挑眉一笑,他向前一步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伸手捏了捏斐玉的脸蛋,高高兴兴道:
“这么多年来师傅都不肯收徒,我也不能摆摆师兄的谱,现在好了,终于有个贴心的小师弟了。”
说到这里,他放下不规矩的手,向穆寻问道:“老师,行简给您贺喜啦,这关门弟子终于给您千挑万选地选了出来啦!”
语不惊人死不休说的就是萧行简,他这话一出来,在座的教谕学生,各个都露出震惊之色!——哈?关门弟子?
第十四回
所谓关门弟子,指的是传道受业解惑的老师所收的最后一名弟子,在这之后便收山不再收嫡传弟子了。
作为最后的弟子,相较于之前所收,老师往往会对他倾其所有,将毕生的本事都交与于他
因此,关门弟子大多都会成为老师的衣钵传人,不仅是老师最为疼爱重视,关爱照顾,在众位弟子中地位也最为特殊。
自穆寻执掌岱殊起所曾教授过的学生难以计数,可以说,只要是曾在书院读过书,听过穆寻的课的,都是他的学道弟子,在外称呼穆寻一声“老师”也不会被嘲笑。
而曾入学天乾堂的学子们,因受穆寻指教最多,按学界的传统,便可称自己为穆寻的入门弟子。
当今仕林还有两位名士与岱殊齐名,这二人尊崇“达则兼济天下”,追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们广招学生,传授本道,收徒也严守规矩,但凡收徒便要行拜师礼广而告之,再从这些拜了师的入门弟子选人收为入室弟子,进而再择嫡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