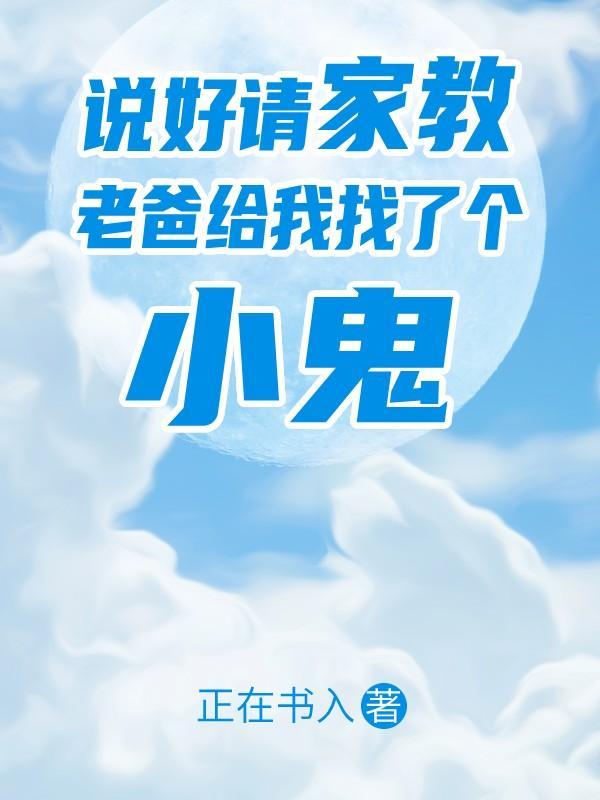风云小说>西柏林的陌生人是he吗 > 第11章(第1页)
第11章(第1页)
第二十二章
柏林墙拆除之后第二年,我去拜访莱纳当年的公寓,更准确来说,是在楼下偷偷仰望它的小阳台和窗户,手里拿着地图,假装是在找路,看了几分钟就走了,免得哪个过分谨慎的邻居报警。阳台上放了两张可爱的白色小木椅,一左一右把圆形咖啡桌夹在中间。卧室窗户挂着斑马纹窗帘,窗台上有一整排养在矿泉水瓶里的植物。我想象一对年轻情侣住在里面,一个起居室,一个卧室,足够容纳他们的生活。出于突如其来的鲁莽和好奇,我折返公寓楼下,门是开着的,早就没有门房了,连门房的住处都租了出去,对着走廊的窗户已经用砖块砌上。我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上站了一会,像个不知所措的客人,确认没有人会跳出来指责我行为可疑,这才走上楼去。
那是个工作日的中午,星期二,也可能是星期三。我敲了敲门,做好了无人应答的打算。很快有人开了门,一个戴着耳机的年轻男人,牛仔裤口袋里塞着一部随身听,他可能本来就在等什么人,脸上挂着笑容,一看见我,笑容就消失了,变成装饰着礼貌的警惕。他摘下耳机,问我想干什么。
“我找比德曼先生。”我随口编了一个名字。
“这里没人叫比德曼。”
在他背后,我能看见起居室。当然翻修过了,换了地板,贴上了柔和的淡橄榄色墙纸。靠墙放着布面沙,旁边的小矮柜上摆着电话,还有一个相框,照片里一对搂抱着的男女对着镜头大笑。果然住着一对情人。天花板也重新油漆过了,一盏球形吊灯像巨大的乳白色虫蛹一样垂挂下来。戴耳机的男人往外走了一步,虚掩上门,阻止我继续窥视。“听着,要是你不确定地址,回去查清楚再来,嗯?我不记得这栋楼里有谁叫比德曼。”
“抱歉。”
“不要紧。”
门关上了,上锁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异常响亮。我还在想那个起居室,在我的脑海里,莱纳的形象仿佛印在半透明的塑料片上,雾蒙蒙的一层,一个剪切下来的幽灵,以拙劣的手法叠加在起居室的图像上。这对情侣一起吃早餐的地方,莱纳曾经站着读报纸。被自行车车轮反复蹭出一道一道黑色痕迹的墙角,现在放着吉他。厨房里不知道还有没有窃听器,像死掉的甲虫一样被遗忘在墙缝里。科里亚的靴子同时踏过新的和旧的地板,在想象中,我看着他把莱纳从卧室里拎出来,拖过尚未存在的长毛绒地毯,让他坐在此刻新租客们摆放电视机的地方。
如果科里亚想来问安德烈的事,那就是浪费时间了,他什么都不知道。莱纳这么告诉科里亚,说得飞快,就像他已经复述这句话很多次一样。
但科里亚不是为此而来。安德烈已经不在他的雷达监控范围里了,很可能再也不会回来。克格勃已经另有打算,科里亚不像“赫尔曼先生”,不喜欢摆出虚假的友善姿态,用二十个设问句引出实际内容,他直接把交易条件摆在莱纳面前:如果不想继续被斯塔西骚扰,那就当克格勃的“渡鸦”。
又是黑话。莱纳已经不能更厌倦黑话,这一个一个原本普通的单词,被强行借用过去,安上阴暗的潜在含义。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在这个只有零星家具的起居室里,他没有逃避的空间,只能躲进自己脑海深处,木无表情。科里亚把这种麻木解读为困惑,开始解释什么叫“渡鸦”,这是性诱饵的代号。克格勃瞄准了一个刚刚从华盛顿调来柏林的美国外交官,这人对此前派出去的三只“燕子”都不感兴趣,是时候试试光谱的另一端了。
相对于女性“燕子”,男性“渡鸦”不太常见,几乎总是勒索的前奏,那一次也不例外。科里亚不愿意用苏联训练的“渡鸦”,他们一旦被捕,克格勃很难摆脱关系,换作其他时候,克格勃也许不介意让人知道,甚至会故意炫耀,但在1956年,隧道事件过后不久,他们不太乐意时隔几个月又制造一场外交危机。莱纳是一份可以随意牺牲的资产,如果一切顺利,那就一切顺利。一旦有什么出错了,克格勃可以轻松把他扔掉,没有什么损失。也许安德烈一开始看上的也是这一点。
“收拾一下你自己。”科里亚说,这个建议从他嘴里说出来,让人不太舒服,“你看起来像只死了两个星期的老鼠。我给你十五分钟,我们有很多准备要做。”
住在一楼的门房想必又一次目睹莱纳被押上汽车,也许马上打电话给斯塔西报告了这件事,说不定也打给中情局,那时候几乎每个柏林线人都同时服务两个以上的主顾。科里亚没有蒙上莱纳的眼睛,目的地并不是什么秘密,那是家酒馆,还没到营业时间,大门紧闭,门上方安装着巨大的霓虹灯管,因为是中午,都没有亮起。“金色鹈鹕”,熄灭的灯管拼出这几个单词,一只金属鹈鹕衔着鱼,站在字母旁边。科里亚带着莱纳从侧门进去,司机没有下来,车门刚关上就把车开走了。
这并不真的是个交易,现在想来,只不过是用一头豺狼换了另一头豺狼。这是莱纳第一次去“金色鹈鹕”,但远远不是最后一次。常客们对他没什么印象,记得莱纳的零星几个人,一致认为他“很安静”,没什么值得一提的特别之处。也许他觉得无助,也许觉得愤怒,又或者什么都不觉得。不过,像他这样一头习惯于服从命令的小羊,再次有人把项圈套到脖子上,也可能是一种解脱。
安德烈并不十分热衷去酒吧,搬到德文郡过一个月了,一次都没有去过。他在埃克塞特一所暮气沉沉的寄宿中学里找到一份教德语的工作,一周上课四天,周一和周三高年级,周二和周四低年级,周末还要监督一大群十四岁男孩在草皮稀疏的院子里踢球。
他用“莫里茨朗格”这个名字,是六处分配给他的,连同一段伪造的人生,附带各种必要的推荐信,证明“朗格”受过良好教育,过去三年受雇于西德一家并不存在的贸易公司,品行正直,富有责任感,如此这般,今年因故返回英国,并且不打算再离开。他还准备好了“为什么回国?”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校长并没有问。校长是个雪茄不离手的小个子,要是不挺起腰,就要消失在办公桌后面了。他养着两只伯恩山犬,面试的时候,那两只壮硕的狗就趴在桌子下面喘气,口水滴在安德烈的皮鞋旁边。
埃克塞特的生活很简单,轻易就形成惯例。学校提供餐点,为了减少和其他人说话,安德烈总是早早地来,在专门留给教师的松木长桌旁匆匆进餐。他不是个严厉的老师,如果学生在他讲解语法的时候睡过去,口水流到动词变位表上,那也无所谓。如无必要,他从不在休息室久待,那地方让他想起霍恩斯比喜欢去的俱乐部,挂着天鹅绒窗帘,充满香烟烟雾,即使白天也很昏暗。疲惫的教师们谈论板球赛得分,季节性暴雨,和本周闹出最大麻烦的那个男孩。安德烈不讨厌也不喜欢男孩们,学生对“朗格先生”报以同样不冷不热的感情。这家中学的大部分学生来自埃克塞特本地,或者附近的城镇,父母可能是渔民、家具商、手工业者,或者新移民。百分之九十的男孩这辈子唯一被迫使用外语的场合就是学校。
有些中学就像低洼地,聚集了被雨水和泛滥河流冲刷下来的各种沉积物。安德烈思忖有多少夹着尾巴回来的间谍最后走进了公学,试图把破碎的德语、法语或者阿拉伯语句子塞进目光呆滞的学生脑子里。安德烈怀疑教世界史的威廉姆斯先生是他的同类,但这只是不太可靠的直觉,他没有证据,也不想去找。故意搅动低洼地里的死水,是一件不礼貌的事。
在其他人老师、门卫、清洁工和教区牧师的印象里,“莫里茨朗格”先生总体而言是个令人愉快的人,举止得体,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校长和门卫,在埃克塞特的几年里,从来没有过绯闻,似乎也从不喝酒。有人声称“朗格先生”在外国结了婚,妻子是个捷克人,因为签证问题来不了英国,但也只是道听途说罢了。从学校保存下来的旧照片里,时常能现“朗格先生”的踪影,但他给观察者留下的要不就是背影,要不就是模糊的侧脸,不过姿势很自然,让人说不清楚到底是巧合,还是他故意躲避拍照。
每隔两周的星期六,是学校的郊游日。老师们轮流带男孩们去远足,钓钓鱼,学些野外生火或者系水手结这样的技能,下雨也不例外,校长深信恶劣天气更能锻炼身心。这是固定行程,如果有人留意观察,不难现这家学校的德文老师每一个月都会出现在同一个露营地,身边围着吵闹的低年级男生。这是个靠近公路的营地,车来来往往,来野餐的人也非常多,春末尤甚,简直像个露天土耳其市集。一个刚搭起来帐篷歪倒了,里面的男孩们尖叫着逃了出来。附近坐着野餐的年轻男女摇摇头,露出宽容的笑容。一个路过的郊游者停下脚步,皱着眉,似乎担心男孩们的安危。
“昨晚下过雨,泥太松软了。”那个郊游者评论道,他戴着玳瑁边眼镜,灰白头从猎帽下面露出一绺。就像其他郊游者,这一个也背着帆布包,手杖末端沾满了泥。安德烈上下打量他,又把目光转回学生身上。
“从伦敦跑到这里远足,不是太远了吗?”
霍恩斯比笑了笑,“来见老朋友的话,不算远。”
“老朋友有电话。如果有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通常不是好事。”
男孩们从泥地里找回绳子,重新拉起帐篷,两个高年级男生把绳子绕在木钉上,深深敲入泥土。滚了一身泥土的学生脱掉上衣和短裤,搭在手臂上,往不远处的小溪走去,几个提着铁皮桶的低年级男孩跟在后面。
“我需要和你谈谈。”霍恩斯比说,看向小溪的方向,“关于柏林,更准确来说,关于‘麻雀’。”
第二十三章
当天在露营地的三十二个男孩里,只有一个留意到了德文老师和戴着眼镜的陌生人交谈,也仅仅是“留意到了”而已。谈了多久?不知道。那两个人一直在露营地,还是中途到别的地方去了?不记得。这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在他年轻的脑袋里停留不到两周,就像沙滩上的脚印一样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