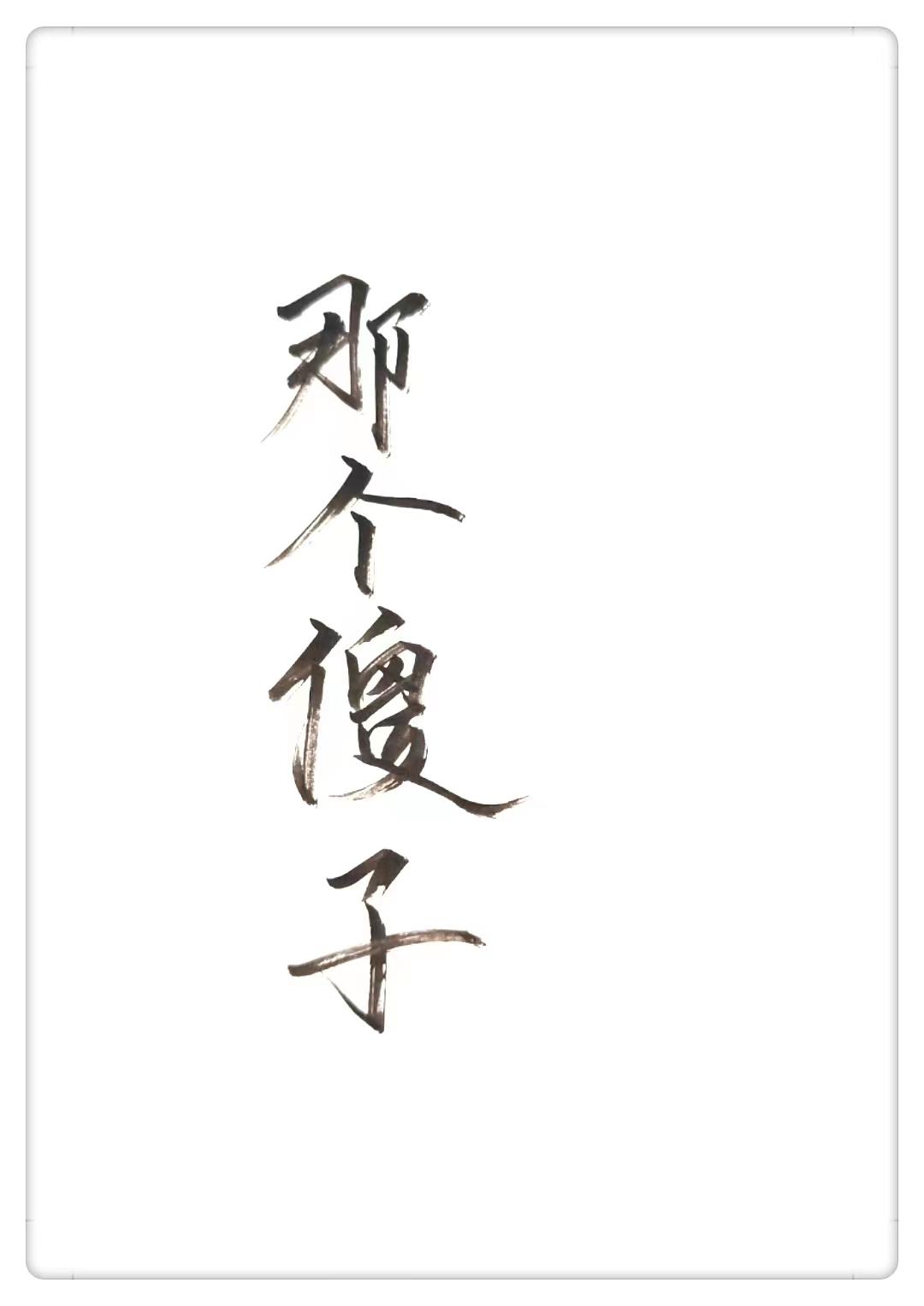风云小说>重生后独宠灾星小夫郎赶山赶海 > 第53章(第2页)
第53章(第2页)
竹筐里添了好几样东西,苏乙抬头看到不远处酒坊的酒招子,转身问钟。
年节里确实不可能不吃酒,不过钟想着今晚是自家吃饭,吃完还要进城看灯,吃的一身酒气多有不好,本想说不打酒了,倏而心思一转道:“不打那等烈酒了,咱们打一斤甜米酒回去。”
苏乙知道甜米酒,几乎称不上是酒,可以拿来煮汤圆子,多是姐儿哥儿喝的,汉子都瞧不上。
以前刘兰草就常说甜米酒好喝,也曾往家里打过几回,不过都是二三两的打,现在得知自己能尝尝,当然是欢喜的。
一斤甜米酒当真不少,他们没带酒壶,竹筒装不下,便多花五文钱买了个酒坊的酒壶,想着以后打酒也能用上,不算浪费。
买到这里就算是差不多了,其余街上的好吃好玩的,今天生意都比往常好,有那吹糖人、捏面人的,早早就把摊子摆上闹市街头,但他们俩都没多看,晚上还要再来,到时再细打量也不迟。
下午回家做酱前,得知他们夫夫二人提前收摊回来了,渐次有人提着小杂鱼来卖。
过去这些小杂鱼随网捕上来,多是各家留下自己吃了,或是实在不想吃的,捡那大的留下晒干存着当口粮,余下的直接丢进海里。
假如拿去乡里圩集卖,一大堆赚不得几文钱,根本不值得跑一趟,遑论现在还要缴鱼税,那真是纯纯赔本生意。
现在不同了,钟家多了这门生意,放出话来说是可以收杂鱼,一斤五文钱,不过不是来多少都要,有时要的多,有时要的少。
村澳里不少人,尤其是离钟家船近的,现在都养成习惯,但凡手里杂鱼多了就来问一嘴,要的话赚两个铜子,不要的话也没什么损失,下回再来问就是了。
像今日钟就收得多,加在一起买了小三十斤的杂鱼,给出近一百个铜板,另外沙蟹、蛤蜊也收,这两样从水上人手里买都价贱,沙蟹三文一斤,蛤蜊肉也是五文。
苏乙起先想不通这个道理,总觉得能自己捕的,何必花钱买别人的,钟春霞也这么觉得,钟只好拆开给他俩算一笔账,就拿沙蟹来说,一斤沙蟹出半斤酱,做成酱卖三文一两,也就是三十文一斤,这部分的本钱才六文钱,蛤蜊酱同理。
让出这几分利,做成酱仍有利可图,把省下来的时间花在别的事上,人也能歇歇。
不然成日连轴转,好人也要累坏了,到时抓药吃药,花的只会更多。
苏乙被他说服,钟春霞就是不乐意也不管用,唐大强同样劝她,钟已是成家立业,有了夫郎还有了自己像样的小买卖,他们当长辈的见识不如小辈广,脑子也不如他们活络了,不如放手让他们自己去折腾。
虾酱、蟹酱和蛤蜊酱,基本都是捣碎磨细后调味封坛,到了时日再启坛方有绝佳风味,其中虾酱还有陈放越久越好的说法。
苏乙特地留了几坛,打算分别过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再开封尝尝。
鱼酱和贝柱酱要架锅炒制,向来都是钟一手包办,做熟练了以后他动作很快,趁着收汁时还能空出手帮着捣酱。
有时候唐莺和唐雀也会来帮忙,若是来了,钟便给他俩工钱,哪里能让人白干。
虽然唐莺还没嫁人,唐雀年纪也还小,但谁不愿意自己手里有些能随意支取的零散铜子,去乡里时能买两块糖、一个炸油饼,或是扯段头绳,买点绣花的彩线。
对此钟春霞更是拦也拦不住,索性不多嘴了,省的被孩子怨怪,说她是嗦嗦的老阿婆。
铁锅里炖着酱,家里几个石臼尽数上阵,捣声不断,钟做到一半,见夫郎和小弟都在揉手腕,他自己力气虽大,忙这半天也觉手酸,遂道:“这也不是个长久之计,既现在卖酱看着是长久营生了,等我从海上回来,就去做个石磨搬回来用。”
农家都有石磨,一个村里至少有一个,磨米磨面磨豆子都用得上,他们水上人不种粮,自也没有添置石磨的。
“那东西沉得很,买了放在哪里?”
苏乙也明白纯靠手捣做得慢的道理,哪怕石磨贵,却和铁锅一样都是值得花的钱。
他以前不知道石磨长什么样,后来在乡里一个豆腐坊见过一回,才知道就是一块沉甸甸,凿出样子的大石头,那东西可以把豆子磨成豆浆,磨虾酱蟹酱定也不在话下。
“放船上自是不可能的,到时放山上石屋里去,我找六叔公打个招呼,放咱们族屋里,别家想用,打个招呼也能借出去用,这样族里人肯定都乐意。”
钟越想越觉得应该早买,不然以后卖酱的生意越来越好,做的都赶不上卖的多。
“下次得空,我找詹九打听打听石磨该去哪里买,一般什么价钱,或是谁家有用旧的,只要没坏,愿意便宜给咱们的话咱们也要。”
从午食后开始忙,两个多时辰后总算将几样酱各自做出一些来,至少往后几日有得卖,像是需要酵几日的,家里已有上次做的一批可以开坛了,等那批卖完,眼底下这批刚好续上。
将其各自装入罐子里后,打水冲干净石臼和船板,小两口坐了一会儿,喝了碗水,继续起来操持晚食。
想到是为了过节吃顿好的,浑身的疲乏皆不算什么,一向不玩到天黑不回船的多多,仿佛也知道今天有好吃的似的,早早就竖着尾巴跑回来,围着几个主人蹭来蹭去,蹭的几人裤腿上一层猫毛。
到了傍晚,几道菜依次上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