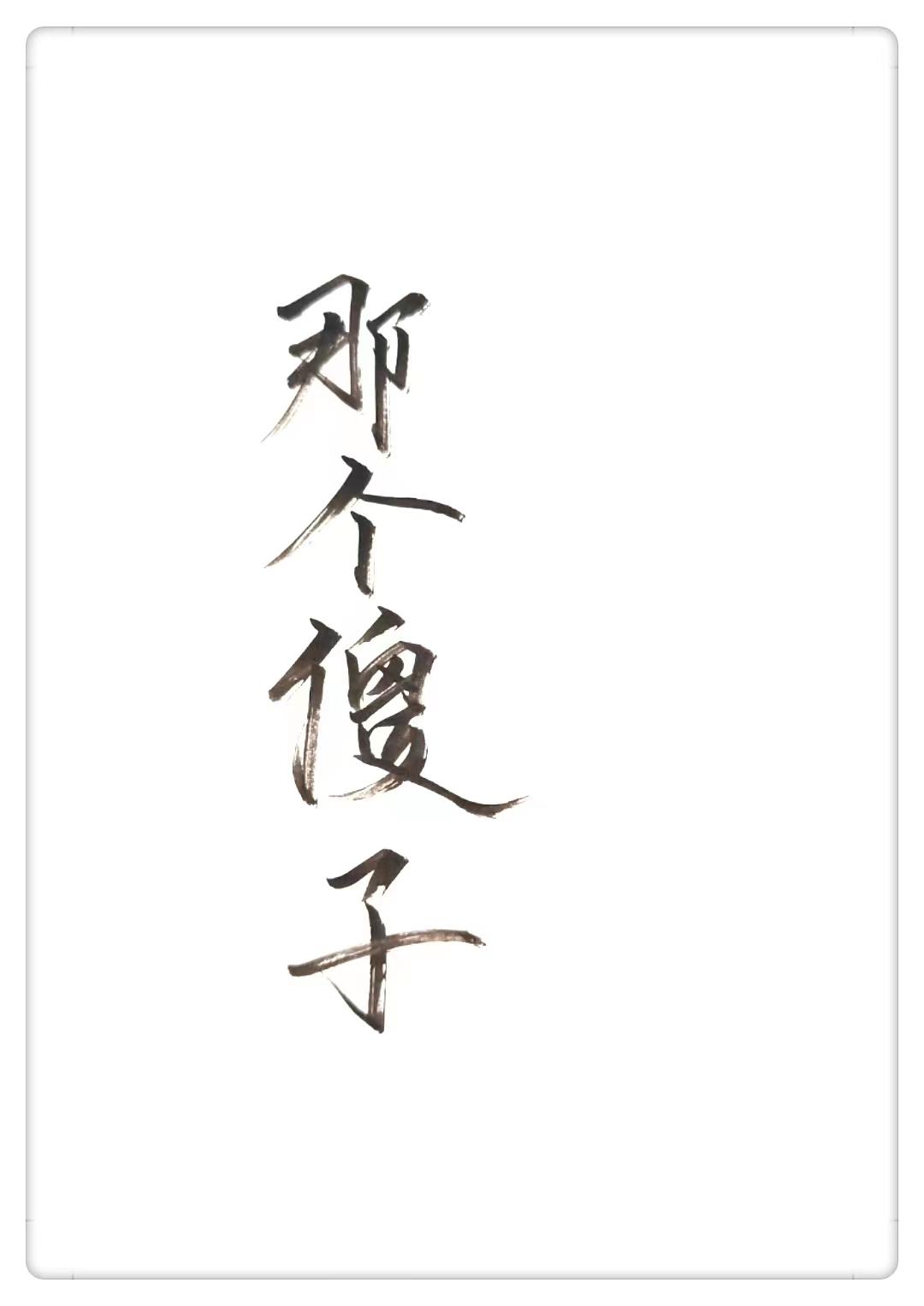风云小说>第七年夏天免费阅读 > 第66章(第2页)
第66章(第2页)
姜守言不敢抬头,他努力睁大眼看着面前堆了半个身子的雪人,却怎么也没办法看清。
是幻觉吗?他想,他最近过的很不好,时梦时醒的。
可是为什么会这么难受呢?他抖着手,想继续团手上的雪人,但捏了好半天雪都团不出来一个完整的形状。
他有些崩溃地发起抖来,视野里突然伸出来一双手,温热宽大,缓缓包裹住他的。
“在堆小雪人吗,姜守言?”
酸涩在心口堆积成了丘壑,眼泪毫无预兆滚了下来。
程在野蹲在他旁边,明明自己也红了鼻尖,还温和着问他:“怎么哭了?”
不远的地方,祁舟和林桓站在街道边,看着依偎在雪地里的两道身影。
他们都穿了白色的羽绒服,几乎和白茫茫的雪地融为一体,却并不显得空茫。
祁舟回忆起那天晚上,他找林桓要了微信号码添加好友,因为过于惊讶这种巧合,验证消息都忘了多解释几句,就着之前保留下来的祁舟两个字发了过去。
发送成功后才觉得太仓促,正想再添加一遍,补充点信息的时候,叮一声响,一个全新的头像弹了出来。
zephyr:你好,请问你是姜守言的朋友么?
祁舟愣了愣,打字道。
祁舟:他跟你提起过我?
zephyr:嗯
程在野没和他多寒暄,开门见山问了很多没办法亲口问姜守言的问题,祁舟一一答了。
他们这样一来一往聊了十几分钟。
祁舟能从字里行间看出程在野对姜守言的关心,这让他觉得放心的同时,又有一点担忧。
感情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时候,都是在争吵和磨合里愈发深刻,他当初和林桓分分合合很多次,才一点点走到了现在。
说实话,每一次分开都挺疼的,他想让姜守言幸福,又不想让他疼。
姜守言从小到大都很安静,安静得让人很容易忽略他其实一直都在承受痛苦,祁舟不认为他还能再经受一次打击。
所以他看着那句“我能来见他吗”,久久没有办法回复。
祁舟想不如就成为念想,吊着姜守言活下去,然后慢慢带他去看病、吃药,等到好一点的时候再见面。
祁舟:他现在的状态不怎么好
zephyr:我知道我知道,我有去看心医生,我有很认真地了解
zephyr:我这几个月一直在跟家庭治疗的项目,焦虑、抑郁、强迫、双向、精分……我都有很认真地学习,从家庭的层面该怎么干预和疏导,怎样和社会重新建立联结
程在野发一条,祁舟愣一会儿,一直到大段的白色聊天框把他的绿框顶上去。
他才终于意识到该回点什么东西,手指刚在聊天框里打下“你真的能接受生了病的”,又突然顿住。
他视线移动,看着程在野发过来的那么多条消息——这个问题已经显而易见,没有必要问了。
祁舟长按删除,又是一条新消息弹了出来。
zephyr:我其实不是第一次见他
zephyr: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七年前,你应该知道吧,姜守言大学来里斯本实习工作了一段时间,那是我第一次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