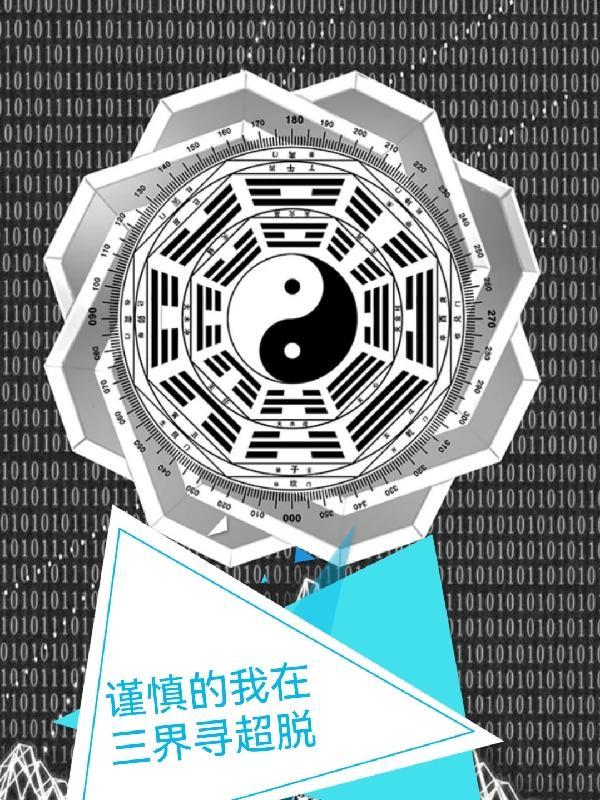风云小说>世子很凶武功排名 > 第46章 新儒学派(第2页)
第46章 新儒学派(第2页)
“我儿就算将来做了燕王,也未必不能像他曾外祖父那样,成为文坛宗师。”
萧素素略显得意。
随即又问陆景兴道:“不知陆祭酒前来北燕,所为第二件事是什么?”
陆景兴道:“如今‘新儒学’越来越兴盛。
我乾京国子监乃大乾最高学府,自然也要开授以新儒学经典为教义的课程。
而天下新儒学最有力倡导者,便是原北燕国子监祭酒,宋审言。
听说十六年前,宋审言因为一篇文章,惹恼北燕王,差点被充军发配。
只因他是北燕第一大儒,在众多门生求情之下,方才戴罪立功,去往西山书院教书。
既然宋审言在燕王眼里,只是一个罪臣。
可否行个方便,让陆某带至乾京国子监,做个博士,专门传授新儒学?”
“你原来是为了宋审言而来?”
萧素素神色冷峻了起来,冷笑着摇了摇头道:“你恐怕要白跑一趟了,我们北燕,绝不会放宋夫子离开?”
“为何?”
陆景兴诧异道:“燕王能因为一篇文章,迁怒于宋审言,将其充军发配,为何不能让他随老夫去往乾京,教授学问?”
“你以为,我家王爷是真的因为一篇文章,才贬斥的宋夫子么?”
“难道不是?”
萧素素神秘地笑了笑道:“宋夫子若不遭到贬斥,堂堂北燕第一大儒,国子监祭酒,如何前来西山书院教学?
他又如何能教授我儿?”
陆景兴听了这话,顿时像遭到雷击一样,愣在当场,久久说不出话来。
过了良久,他才嘴唇微微颤抖道:“老夫明白了。
宋审言得罪燕王是假,让他前来教授世子是真。”
萧素素缓缓道:“十六年前,我儿刚刚出生,王爷便定下了穷养策略,带我母子去民间,过平民生活。
但生活可以节俭,对儿子培养却不能马虎。
必须挑选天下最顶级大儒前来教授。
时任国子监祭酒的宋审言,便是不二人选。”
陆景兴不忿地接口道:“所以燕王便借题发挥,故意生气,将宋夫子贬斥至西山书院。
可是如此对待一位大儒,将其玩弄于股掌之间,岂非不公平?”
“哪里不公平了?”萧素素淡然道:“宋审言不知不觉间,已经做了十数年世子少师,将来我儿登上王位,岂能亏待了他?
如今受多少苦,将来我儿都能补回来。
宋夫子半个身子,已经坐上燕国国相宝座,岂能跟你离开?”
“那倒也是,”陆景兴长叹一口气,点点头道:“看来老夫是白跑一趟了。”
“你也不算白跑一趟,”萧素素道,“我儿马上就要参加童子试,陆世叔作为天下第一大儒,可以指点一下我儿,好让他考试通过。”
陆景兴苦笑着道:“世子作为新儒学派的开山鼻祖,却为了童子试而发愁,此事传扬出去,岂不令人可笑?”
萧素素道,“童子试如何选拔,本宫也不知道,既然陆世叔到了,不妨给指点一二。”
“既然如此,老夫就勉为其难,献丑了。”
陆景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