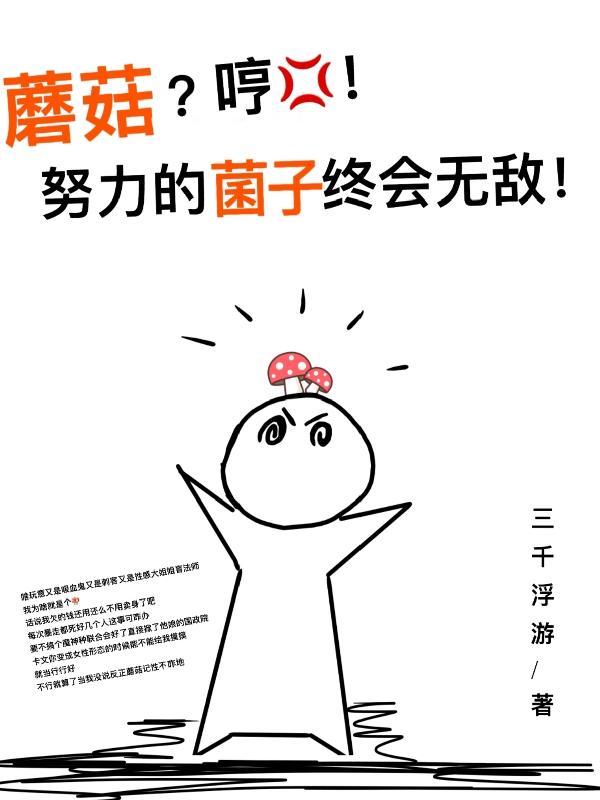风云小说>8月凉山 > 第85章 天星预言(第1页)
第85章 天星预言(第1页)
《明王真经》原本一直待在计雪然的怀中,五年来不曾离身,早已习惯。可是此时,经书如一块巨石,压在了计雪然的心上。经书,不单是一本经书,早已变成了责任,或许是信任。
父母的仇恨,山庄的安危,孔雀谷的宏图,件件责任已经让计雪然难以喘气,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似乎夹杂着一丝绝望,何种的绝望?累了,怕了而已。
“不!”计雪然心中那股委屈大声的嘶喊,“我不是什么星将!我只想为爹娘报仇,我不是什么乱天的凶星,更不是那拯救苍生的善星!我不做!”黑暗中,那颗倔强的心无力的呐喊,无人听到,但却诠释了无奈的心境。
“外公?”方化的身形忽然出现在脑中,计雪然浑身一震,想起了儿时修行情形。那颗不屈的顽灵痛苦的哭诉:“外公,您也知道么?为什么…雪然累了!”
血泪,自心中四处流淌,完美的外表之下,倔强的心灵已莫名的遍体鳞伤。良久,良久,那无力的呐喊消失在心际,只留下那血泪的痕迹告知着自己,我曾来过。
初六坐于计雪然的身旁,见计雪然也不做声,神情恍惚的呆在那里,有些焦急,不忍道:“雪然?”
化黎禅师脸色平稳,不见异样,开口道:“计施主,你也切勿忧心,以你的出身及品性,贫僧和师兄都看在心中,故才将《明王真经》赠予施主,想来加以时日,施主必定成为人间的福气。”
计雪然转过神色,僵硬的望着化黎禅师那枯瘦的面容,薄唇颤抖:“大师,您为何说我便是那星将?难道老祖宗曾有言透露?”
化黎禅师听言,摇摇面,沉声道:“阿弥陀佛,佛祖有曰,不可说,不可说。施主请恕老衲不便相告,此乃天机,老衲已经破例,若再多些透露,恐怕天道变化,到时便不是我等所能预见的了。总之,计施主,《明王真经》乃是我明王寺相传之宝,但其并不是以修行为重,最之珍贵的,乃是其修心之理,修行路上,长远漫漫,切勿不可焦躁,真经有庇护心脉,安稳心神之效,施主需铭记在心。”
化黎慢慢道来,言者有意,听者却无心,计雪然根本思索不下化黎的言语,脑中恍惚,无力感充斥全身,此时就连此行的目的也都忘却。见计雪然与方才拍若两人,初六有些不忍,也不顾着尊卑,抢言道:“师父,雪然今日劳累,本有要事要办的,若师父没有其他事情,不如让雪然先去歇息吧?”
化黎禅师别过脸来,淡淡望向初六,初六眼中期待,对着化黎禅师的面容,充满了恳求。一旁计雪然,面色依旧不变,恍恍惚惚,眼中神色呆滞。化黎禅师看在眼中,也现出几丝不忍,叹气道:“施主,此事突然,我同师兄本欲过些年数再予相告,但师兄总有预见,我二人不久便要走到尽头,贫僧也是无奈之举,只望施主能顺其自然,安心修行,有终一日,定成大业。”
这番言语,渗透着丝丝的悲凉,计雪然心神微微回转,眼光闪现出几分光芒,不禁道:“大师,您同方丈大师修为通天,怎会…”
化黎禅师念诵一声佛语,缓缓摇头。计雪然不明,向两边望去,初六低头不语,但露出的面容却夹杂着悲痛,而一旁初水则神情自若,见计雪然望来,反倒开口:“计施主也知吾师同师叔修为几乎参通天晓,自然对生死也有预知。不过万物生灵,终有尽头,施主也无需难过。”
化黎禅师听言点头,满意的望着初水,道:“初水所言甚是,初六,你要同你师兄多加学习。计施主,贫僧所做,只有如此,日后,便要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计雪然伤痕的心中又丝丝作痛。面前,这天下闻名的神僧,竟然已经到了油灯耗尽之时,不过便是到此,他还不忘关切自己,计雪然眼前有些生涩,那倔强的骨子再也压制不住心灵中的脆弱,若不是强行的矜持,恐怕银花便要从眼中流出。
干涩的薄唇微微一闭,复而张开,颤音从口中出:“大师,雪然定当紧记您同方丈大师的教导,大师,请受雪然一拜!”计雪然神情激动,疾站起,心中那良久的无力暂时消退,感激之情冲上心表。
化黎禅师听言赶忙伸手,可还未有所动作,计雪然已经离座跪下,清脆的声响从计雪然的额头处来。
化黎禅师长叹一声,一股柔劲涌来,计雪然只感有人拉扶,站身起来。
“计施主不可如此,你能有此之心,实可证明你心中善念磅礴,我同师兄,总算没有看错人。”
计雪然见化黎只是真气渡过便将自己扶起,心中暗暗佩服,感激道:“大师同方丈大师能相告雪然,雪然已是感激不敬,单是这份恩情,雪然也会竭尽所能。”
化黎禅师终于含笑点头,道:“阿弥陀佛,孩子,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心有善念,永传人间。记住老衲的这些话,去吧…”
计雪然心中默念,深深印烙脑海,他再见化黎,化黎禅师含笑点,那枯黄的面容上满是皱纹,此时却是那般的苍老,心中莫名一痛,计雪然打了一礼,道:“大师早些歇息,雪然告辞,日后雪然定会再来拜访。”
化黎禅师眼中神光复杂,那白枯的老唇微张,却始终没有再出声响,他别过视线,缓闭上了双目,苍老的面庞在烛光之下轻点,久久之后,停歇下来。
初六初水见此,从坐垫上站起,计雪然大作一礼,不舍的转过了身子,随着初水二人走出门外。三人站立门外,初水身在最后,伸手去关上那扇僵硬的房门,计雪然终究忍耐不住,向门中望去。
烛光闪烁,好如被凉风吹拂,几欲熄灭,化黎禅师那瘦弱的身形忽闪在微弱的烛光中,寂寞,凄凉。无情的房门终于在初水手中合上,心中那丝期待却换来无比的失落,失落过后,那昏暗的烛火映过纸窗,泯灭在黑暗。
夜,深了,深的月儿那般光亮。风,静了,静的脚步如此响亮。三人轻声慢步,沉默不语,走在路上,许久之后,又来到那庭院之中。
青鼎之内,香烟已然烧尽,消失的找不到踪迹,偌大的庭院之内,除却这尊青鼎,好像就只有苍生存在。不知为何,夏日的夜晚竟却没有一丝风响,但苍生那苍劲寂寞的身影,在月光下独自摇摆,反抗着静夜的凄凉。
计雪然走在最前,三人悄无声息,逐一漫步苍生脚下。初六不甘这沉闷的寂静,破口道:“师兄,你今日怎有空来大悲院?”
初六开言,三人各自转身,面面相对,初水一笑,道:“今日凌晨,师父便唤我前去,说大悲院定有贵客前来,命我前来转告师叔,没想到竟是雪然。”初水笑望计雪然,放开了许多,便是从称呼上,也改变了以往。
初六听言,脸上平静,叹了口长气,似乎还沉浸在未知的悲痛中。计雪然站立中央,抬眼望着苍生的枝干,恍惚言道:“方丈大师实乃神佛,便是这等小事也能预知,可…”
初水转淡笑,自然接口:“怎会面临圆寂之境?”计雪然尴尬张口,却说不出下话。初水摇头,笑道:“雪然,你无需如此,若说常人来访,师父便是成了神佛,也不可预见,原因,可全是在你这星将身上。”
“请恕雪然不懂。”计雪然讶然奇言,初水点道:“不错,你身为星将之命,与天上繁星一一照应,尊师便是从星象中感悟,雪然恐怕不知,境界如尊师之境,不去观望,便能有所感知,冥冥之中,已有定数。”
胸口凉意阵阵,苍松古泪感到了计雪然心中那丝奇异的跳动,传来了久违的安抚。计雪然心境安宁许多,但却忘不掉疑问,自控不住,又问:“初水师兄,你可知,为何大师认定,我便是那星将?老祖宗曾说过吗?”
初水面容一僵,眼神有意的避开了身边,望向了上方苍生的枝条。计雪然询问无果,长叹口气,一旁初六呆头呆脑,而内心中却不愿看计雪然这般表情,他移来几步,向着初水问道:“师兄,雪然既然本为星将,也应知晓缘由,初六不知此事,师兄,你不妨告知雪然吧?”
计雪然浑身一震,感激的望向初六,在他心中,初六永远都是那个善良的哥哥,还未等初水言语,计雪然已然笑道:“初六哥,你的好意雪然心领了,其实我既然已是星将,缘由也已不再重要,不再为难初水师兄了。”
初水面色一转,有些惊讶的望向计雪然,初六还欲开口,但见计雪然那淡然的表情,无名之力将心中直言埋没。
“阿弥陀佛,罢了,虽不敢道破天机,但若不透露些许,倒显得初水凭的小气了。”初水笑颜,望过二人。初六听言大喜,傻笑开来。而一旁计雪然面露惊奇,不知该如何开口。初水面对苍生,有前走几步,慢慢道来:“诸葛前辈当日虽然预言,但也绝无可能指明星将便是雪然,天机茫茫,谁又能真正参透。不过诸葛前辈虽然生命有限,但他却将鉴别之法教给了一位长寿好友。如今星将一事,自也不是尊师同师叔所能看出,而是出自那位长寿前辈的见地。”
计雪然今夜被突如其来的消息已经震惊万分,不想如今再次惊骇,他不敢置信,颤颤问道:“老祖宗已逝去将近四百年之久,那前辈…岂不活了四百年了?”
初六一旁锁眉深思,口中念叨:“难道是妖?”
初水听言,失声笑道:“师弟糊涂,诸葛前辈怎会同妖宗结交朋友。至于这前辈的身份,却是不可再说了,否则,天机大变,我成了罪人无妨,对雪然,可就不得想象了。”
初六挠头思索,不知在想些什么。计雪然心中狂想江湖前辈,一时也思索不起到底何人,但初水此番已经道破,计雪然自当是感激不敬,谢道:“多谢初水师兄相告!雪然感激不敬!”
初水笑笑,又道:“雪然此言差矣,我何曾说过何事?”
“呃…呵呵,对,初水师兄所言极是,我等方才只是闲谈,初六哥,雪然可否说错?”
二人相视一笑,望向初六,初六眼中疑惑,一边用手挠头,一边问道:“方才不是这般说的…你们…”
二人面面相觑,放声大笑,只有初六一旁疑惑的望着二人,心中狂问自己,哪般错了。欢笑如此不羁,掩埋了内心那份无助。夜里没有了冷风,总让人有不习惯的舒适,哪怕仅仅是轻风,也能让那熟知的心中泛下几丝波澜。
没有了夜风,黑夜似乎显得格外沉静。没有了夜风,黑夜似乎出奇的明朗。当空之上,金月高挂,繁星厌倦了点缀似的的闪烁,倔强的亮着。月儿那稍稍残缺的半边,隐隐现着片黑影,诠释了最美的残缺。
黄土暗夜,月光洒满了庭院下的土地;静夜无声,笑意充斥了每丝的天地。苍生古松,青枝微亮,在无风的半空独自摇晃,应和般撤去了多年的寂寞,沧桑千年,古松,也成了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