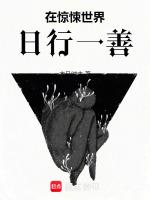风云小说>良妻风浅 > 第67页(第2页)
第67页(第2页)
白云暖目送着他们走远的背影,这才对心砚道:“以后大可不必如此畏缩,你如果心里真的放下了,少爷少夫人跟前就应大大方方的。低头做什么,只管抬起头来。”
心砚这才抬起头,涨红了脸。
于是二人进了别院。
※
别院内,刘郎中已经替姜湖包扎好了伤口,并开了些消炎防脓的药方。
秦艽引着刘郎中走出厢房,迎面遇到白云暖和心砚。
刘郎中虽然口里狡辩,但心里对白云暖已经佩服至极,见白云暖身着粉色雪纺衣裳,翩然走来,犹若天外飞仙,忙拱手作揖。
白云暖也还了礼,对心砚使了个眼色,心砚便止了脚步,未随她进别院厢房,而是折转身子随秦艽和刘郎中走了出去。
等刘郎中领了诊金,心砚便道:“刘大夫,我家小姐请大夫稍候片刻,她有话问你。”
刘郎中觉得和白家小姐谋了两次面,的确和平生所见闺阁小姐大不相同,便随了心砚到听雨轩厅里候着。
白云暖进了客房,见房内二舅二舅母俱在,三表哥手上缠着纱布,隐隐有血丝渗出。比那纱布血丝更红的是二舅母和三表哥的眼睛。
想来二人昨夜都睡得不好。
白云暖上前见过二舅二舅母,便询问三表哥伤情,二舅道:“不碍事,一点皮肉伤。”
二舅母却话里带刺,“他就是脑子糊涂的,竟为了旁人忤逆父母,伤害自己,有道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他真是鬼迷心窍了。”
话说得再明显不过,白云暖听了心里堵得慌。
一直不吭声,憋着一股子气的姜湖终于开口道:“刚好阿暖也来了,我就把话挑明了,父亲母亲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我姜湖此生非阿暖不娶。”
一句话令房内气氛顿时尴尬起来。
白云暖脸上很是挂不住,而二舅原不反对,却因二舅母执意反对,昨夜还在被窝中闹了一晚上别扭,此刻也不敢说出赞同的话,只是黑沉着脸,闷不吭声。
二舅母遂骂姜湖道:“你这混账东西,婚姻大事岂是儿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怎能由得你想娶谁就娶谁?”
二舅母言语很是伤人,仿佛对白云暖做她儿戏很是嫌弃似的。
白云暖不悦道:“非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得问问我的意见不是?我才是当事人哪!”
白云暖一句话,三表哥巴巴地投过目光来。
二舅母忙劝道:“阿暖,你先前同二舅母说过的,你还小,恐你父亲母亲要多留你几年,如此就耽误了你三表哥韶光……”
“母亲,你让表妹自己说。”姜湖生气地打断二舅母的话。
白云暖却漫不经心道:“二舅母说的这个原因不过是阿暖的推托之词。”
姜湖一头雾水,急道:“表妹,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襄王有梦,神女无心。”说着不再看三表哥错愕的表情,径自离了客房。
要不是二舅母言语间多奚落之意,自己也不会明着让三表哥下不来台。
站在客房门外,听见屋内二舅母郁闷不平的声音:“你们听听,阿暖这孩子说的是什么话,她竟还看不上咱们姜湖吗?”
白云暖在心里冷嗤:就兴你挤兑别人家孩子,就不许我挤兑你家孩子?两个舅母比起来,还是大舅母厚道些。不论三表哥喝了酒就混闹的性子,就冲你这有些尖酸的婆婆,我也不稀罕做你们家媳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