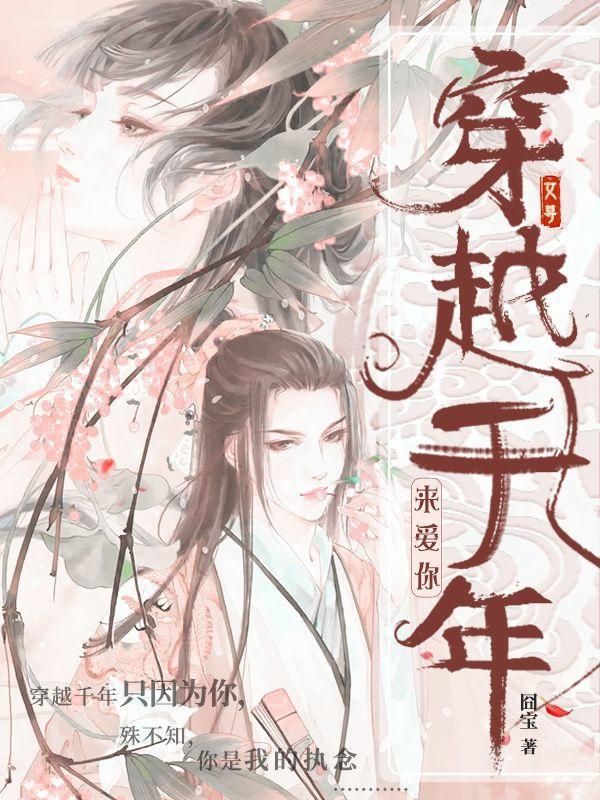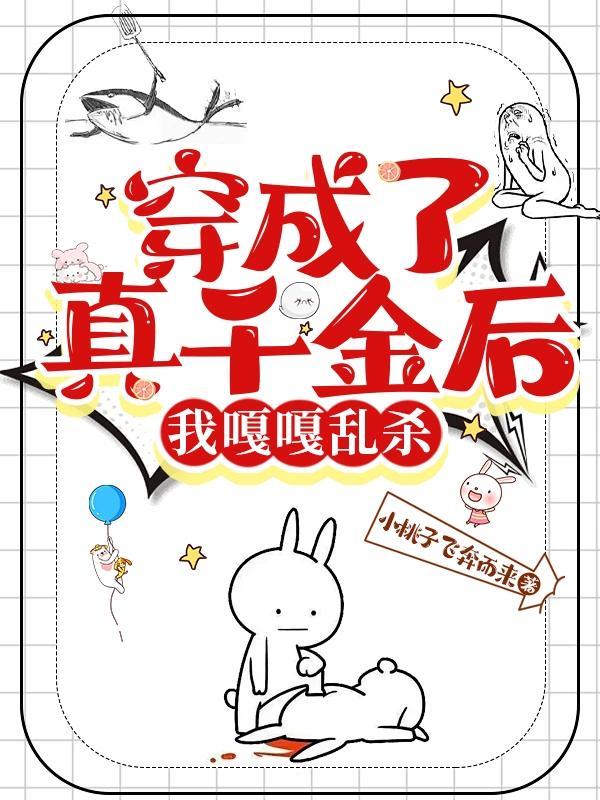风云小说>嫁给枭雄的日子 > 第23章 善意(第2页)
第23章 善意(第2页)
因年少气盛,还抬着下巴,向苏若兰居高临下地道“你是在外揣测,我却将里面情形瞧得明白。小爷这双眼睛不瞎,若真有越矩的事,小爷难道会看不见”见苏若兰脸上变色,似有心虚之状,大声道“说话呀”
这一声斥责,虽不像傅煜冷厉,却也足以让苏若兰胆战心惊。
她打死都没想到,那日街头偶遇,除了她和金灯,竟还有旁人在场。
而那个人,竟还是傅昭
如今当堂对证,若是个丫鬟仆从,她还敢斗胆拿捏,却哪有底气跟傅昭争
比起她揣测激怒的把戏,傅昭那些话近乎铁证,将她的言辞尽数推翻。
苏若兰心虚慌乱,正想着怎么把那些添油加醋的话圆过去,眼前衣袍微晃,傅煜那双黑靴跨到两步外,冷厉威压的气势亦如千钧般悬到了头顶。她甚至不敢抬头去看,只跪在地上,颤声道“将军,奴婢确实没撒谎,奴婢是真的看见”
“放肆”傅煜沉声,如闷雷响在头顶。
他忽然抬手,腰间短剑微翻,径直抵在她颚下。
那短剑是冷铁煅造,刀鞘上缂丝细密,即便在此燥热屋中,也是冷意瘆人。
苏若兰吓得打个机灵,脑海里一瞬空白,手脚动都不敢动。
傅煜轻按剑柄,迫得苏若兰抬头,目光锋锐如同寒冰,“谁教你造谣生事”
“将军息怒,奴婢、奴婢”苏若兰战战兢兢,却是躲闪着,半个字都说不出来。原本颇为俏丽出挑的一张脸蛋,此刻也惊得面无血色,纵打扮得伶俐动人,瑟缩求饶的姿态却叫人生厌。
这般惊慌之下,心虚之态已难掩藏。
傅煜眼底尽是嫌恶,瞥向老夫人时,微微皱眉,有些作难。
而后,又看向攸桐。
攸桐却没看他,只望着老夫人。
方才傅昭那番话就跟闷雷积攒许久后的暴雨一般,将她身上的淤泥灰尘冲刷干净。
不止苏若兰噤若寒蝉,就连老夫人都没了言辞
先前咄咄逼人地训斥,老夫人倚仗的便是苏若兰的言辞,如今活生生被打脸,儿孙跟前,哪能不难堪她的年事已高,侧身坐在那里,脊背微微佝偻,堆满沟壑的脸上老态毕露。兴许是担心傅煜追问前情,在两个孙儿跟前不好圆话,连瓜田李下、避嫌留意的话都不提了,只偏过头,沉目微怒。
攸桐心情颇为复杂。
垂暮之年的老人,有老而睿智的,也有老而昏聩的,哪怕英明神武、杀伐决断的帝王,也有人晚节不保。老夫人深居内宅,到了七十高龄,又时常身体抱恙,能有几分沉稳平日里虽不满,却能相安无事,被有心人一激,便易怒偏颇,情绪激动。
苏若兰这般胆大,也未必不是瞅准了这点,借着老夫人的不满生事,妄想借刀杀人。
闹到这地步,老夫人若下不来台,昏倒在地装个病,便能轻易倒打一耙。
但连番生事的苏若兰,岂能轻易放过
从南楼初见至今,小仇小怨已然积攒太久,她先前特意去两书阁,便是为防着今日之事。如今真相已明,苏若兰跪伏在地,眼巴巴瞧着老夫人,难道还指望博来一条生路
攸桐慢条斯理地挽着衣袖,往前半步。
“无话可说了”她开口,站得居高临下,“先前在南楼时,你便搬弄是非,受了责罚也不知道悔改,如今又跑到老夫人跟前混淆视听为你这狭隘偏见,折腾得鸡犬不宁,老夫人更是气得”
她故意顿了下。
那边老夫人暗觉难堪,又担心攸桐会跟刚才似的穷追不舍,闹得她也没脸,正考虑如何收拾残局,听见这话,下意识抬头瞧过来。
便见攸桐话锋一转,道“你对我有偏见,只管寻我就是。老夫人于你恩重如山,却这般谗言欺瞒,竟半点不念主仆之情”话到末尾,已然带了厉色。
苏若兰想辩白,抬起头便对上攸桐的目光,是从未见过的锋锐。
攸桐也不待她废话,转身朝老夫人道“方才孙媳无端蒙冤,心里着急,若有言语不当之处,还请您担待。您叮嘱的哪些话,往后也会记在心上,时刻留意。”
说罢,浅浅行个礼。
老夫人万万没料到攸桐居然会主动递来台阶,登时愣住了。
旁边傅煜也觉意外,愕然盯向她。
还是沈氏反应快,忙帮着打圆场“这苏若兰真是因你是寿安堂出来的,才信重几分,谁知死性不改,竟欺瞒到了老夫人头上瞧这事闹得,险些错怪了人。老夫人身子骨本就不好,被你气成这样,若有个岔子,谁担待得起佛珠快去请郎中来瞧瞧。”
竟是顺着攸桐的暗示,将罪名尽数推到了苏若兰头上。
老夫人愣怔片刻,意外地打量了攸桐两眼,才就坡下驴道“把她带到柴房关着,等得空时重重惩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