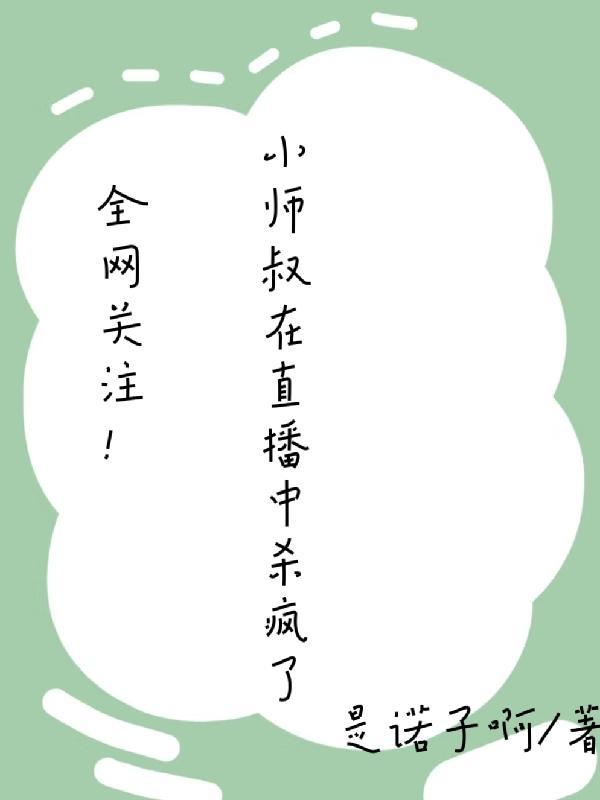风云小说>大明女医纪事无弹窗免费阅读 > 第81章(第1页)
第81章(第1页)
顾清稚回想今日一早即赴裕王府为朱翊钧诊积食病,又看罢礼部?放榜方才归家,连他的身体如何也疏忽了。
一忆及他从前因病告假离开翰林院,在荆楚之地留了数年方才回京,健康状况实在令人担忧。越思脸色越发?不佳,她?敛起眉目,正色道:“相公为何这般不爱惜自己身体,连生病也不肯从实说来?”
张居正不以为意,仍是神色自若,从庭前步回屋中:“七娘无需为我?挂心?,偶感微恙也是难免。”
“不行。”这态度让顾清稚心?里愈加着?慌,加快步子追上前,“微恙久拖即成大病,太岳这般讳疾忌医,到时?病入膏肓了别说我?,便是华佗再世也难治。”
“那七娘说该如何?”张居正神色颇为无奈,但仍望向她?。
顾清稚认真道:“太岳不想和我?白发?满头么?”
“何须问。”
她?笑起来:“那你这般忽视身体,是不想和我?共度一辈子了么?”
“你又胡言。”
他竟失神了片刻,沉黑的眼?眸陷入一瞬的迷惘。
——原来自己是如此恐惧与她?中道相别。
未发?觉他的异样,顾清稚攥住他的手腕贴近自己:“让顾大夫来给张先?生诊诊脉,这儿有个随叫随到的家庭医生,张先?生却不知?充分利用。”
张居正视着?她?手指按压住自己的脉搏,仿佛握住了他那根连通心?脏的经络,沉浮起落皆由她?掌控。
“相公想学吗?”顾清稚忽而?问道,打破其出神。
“你肯教么?”
“只要是相公有心?,我?愿倾囊相授。”顾清稚粲然露齿,指点道,“其实,无论是诊哪边手都没?有妨碍,只需寸关尺对准即可。”
“顾大夫可否先?告知?,我?这是甚么脉?”
“张先?生这是……”
她?垂首沉思了一会儿,张居正以为她?必要说些高深晦涩的脉象言辞,不想她?忽然扬起脸,语出惊人:“滑脉。”
“高肃卿独断专行,才入阁就拿爹不放入眼里,爹再如?何说也是朝中老臣,怎好被他一个后辈如此欺侮!”徐璠怒气如?火,甫归家便朝徐阶抱怨。
徐阶眼一横,不?应他,却是瞪向仆役:“你家大娘子呢?大郎发酒疯,大娘子就坐视不?管吗?”
“是是。”仆役喏喏。
半晌后,请来的却是急匆匆赶来的张氏。
“大郎还不?快回去安寝?杵在这等着你老子发火么?”张氏立定喝道。
徐璠却不?依,仍横眉冷对:“爹一辈子忍让惯了?,先前被严嵩骇得?发不?出脾气,如?今好容易翻了?身,遇上高拱这等气势凌人还是一味退避,这朝中谁还当爹是阁老重臣?他高拱还是爹举荐入的阁,倒端了?副首辅做派,真是反了?!”
张氏不?知事情来龙去脉,于是悄声问身旁一语不?发的徐阿四,后者?见是主母问起,犹豫了?会儿方才道出缘由:起因是今日内阁因为黄河水患议论对策,高拱意见与?徐阶相佐,李春芳等辈素来应和徐阶,他要往东李决不?会往西,奈何这高拱是个刺儿头,硬是和老前辈杠上了?,非要争个高低之分。
徐阶平日素来谦和待下,面对高拱争强好胜也未多言语,甚至一切皆顺其?意。
然阁中谁不?议论高拱性情急躁,以下犯上,这徐阁老也是温文?惯了?,面对如?此?冒犯不?敬也能忍耐得?住。
话传进徐璠耳朵里?,做儿子的自然替爹不?忿,平日里?最是寡言少语的稳重性子,现下也忍不?住要替徐阶打抱不?平。
“朝中谁不?替爹委屈?谁瞧得?上高拱那狂妄之态!那张居正竟还与?这忘恩负义之辈交好!他也不?看看自己老师是谁,真是忘了?本了?!”徐璠一气之下,竟牵连至与?此?事毫无?干系的人身上来。
张氏眉头一皱,厉声道:“还不?快把?你的嘴闭上!来人,扶大郎下去歇着。”
候着徐璠被几个小厮半推半拽地拖走,张氏方覆上愁容,走至低头沉思不?语的徐阶身边,蹙眉道:“老爷当真没有法子么?我想着这般任由那高拱占尽上风也不?好,再怎么说老爷也是首辅之尊,若无?威严,臣下怎生信服你?”
徐阶以指揉捏眉心,显然也是头痛至极:“我何尝不?知?起初推荐高拱入阁也是看中其?确实有才干,且原先待我还算恭敬,我想着自己是无?心志担当大明中兴的重任了?,且看他或许能挑起。怎知此?人一入阁即这般情态,教我如?何能料到?方今后悔也是来不?及了?,我若不?退让半步,只怕他愈发得?寸进尺。“
张氏亦叹气:“老爷难处我也明白,内阁里?有他在,只怕你是难顺心了?。”
“罢了?罢了?。”徐阶长吁一声,复又躺回榻上,疲倦闭目,“我将近七十的人了?,还能坐几天首辅的位置?这天下终归是他们的,我如?今忝居一日是一日,等哪天上疏乞休,这副老骨头若是能终老在松江,也是我徐阶的福气。”
张氏伤感,望着这一家之主白须横生,斜斜倚在颈侧,心内无?端涌起一阵酸楚。
“夫君年轻时何等志向?,如?今却只盼着能乞骸骨回乡,当年可曾想到有今日?”她悠悠感慨,“这朝堂啊,真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何年何月是个头呢。”
“只要有人在一日,就莫想着猜到明日还能否卧在这张榻上。”徐阶透过窗户纸遥看月夜清辉,那浅淡银色悄然撒在面颊褶痕之间,“人心都易变,能坚守的有几个?我大明朝哪里?还有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