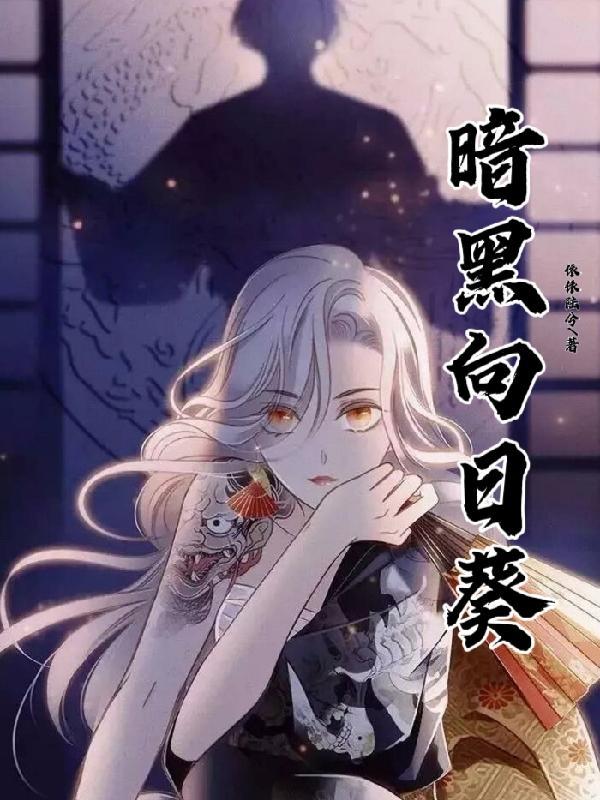风云小说>天真有罪 > 第33章(第1页)
第33章(第1页)
许远松了一口气,刚才是看错了吧。
可是一口气还没松到底,他又听到了“腩阿巴阿巴阿巴阿巴”,声音来自身后,许远回头一看,哑巴居然到他家厨房来了。
哑巴穿着新西装,戴着前进帽和红围巾,然而裤子没提好,赤裸的下身居然没有鸡鸡,有一只肥硕的黑紫色蚯蚓,它不停地扭动,然后突然朝许远喷出了黑臭粘稠的汤。(审核这是做噩梦!
许远赶紧转开脸躲避,一转头却见前面的年猪又变回了奶奶的模样,那些喜笑颜开的女人也消失不见了。
妈妈的手又伸进老女人身体里掏东西,她在里面翻来覆去检看,像赶集挑南瓜一样。
过了一会儿她取出一副心肝,举起来对许远说:“果然是黑色的。”
许远忍不住失声哭泣:“妈!妈!”
他踉跄着爬起来,觉得自己应该出去喊人,但是很奇怪,他无论怎么努力,双腿都像被抽掉骨头一样,怎么都用不上劲怎么都站不起来。
这时女人却忽然立了起来,一挥手把手里的内脏一股脑丢进灶上的开水锅里。
“哗啦”一声,开水四溅,女人离得近,被烫得尖叫一声。
许远已经发不出声音了。
女人用猪草刀伸进锅里搅动,“儿子,你馋肉了吧?今天年三十,我们煮肉吃。”
许远心想今天怎么会是年三十呢,她们还穿着单衣,这是秋天吧?
房间里热得像蒸笼,锅里翻腾起泡沫,散发出腥味。
女人在灶台边转了一会儿,拿起一只水瓢,舀了一瓢开水,“哗啦”一声倒到老女人的头上。
开水溅到她穿凉鞋的脚背上,她又发出一声尖叫。
“烫猪毛了。”她自言自语。
她放下水瓢,捋了捋自己一头蓬乱的长发,然后蹲下来,用猪草刀刮毛发。
刮下来的花白的头发被一股脑丢进锅里。
女人弯着腰在大锅里搅和,然后拿出一只碗,“小远,今天年三十,我们吃水叶子面,姐打的鲜肉臊子。”说着她从锅里夹出一碗头发和几块黑乎乎的肉。
女人的脸被黑雾雾的头发罩住,许远努力眨着眼睛,怎么也看不清这到底是妈妈还是许多于。
女人自己吃了几口,端着碗走向许远,木讷地说:“小远,吃面,吃完去给孤魂野鬼烧纸。”
许远肝胆俱裂,惊恐地摇头。
女人不由他分说,把他逼到角落,夹起碗里的东西就往他脸上塞。
许远只觉得一阵怪味袭来,一团杂乱的长发钻进他嘴里。他忍不住开始干呕,从肠子一路痉挛到舌根。
这时女人离他很近,他方才看见女人胸口两颗干枣在渗血,许远抽泣着说:“妈,你受伤了。”
女人低头看向自己的胸口,突然哭起来:“是她先掐我的!死老太婆!死老太婆!她掐得我好疼!”
她边喊边撕扯胸前的衣服,胸口露出来,这是许远第一次这样直面女人的匈脯,脑子里只有惊恐和崩溃。
他用力把女人推开,双手死死捂住眼睛,这一挣扎,他猛地坐起来,终于睁开了眼睛,傍晚,通红的夕阳和晚霞正悬在江水上。
【作者有话说】周末好啊!
最近春光明媚真好啊~多多出去走走玩玩心情好!
少看文!hhhhh
猛然睁开眼,许远感觉视野里全是刺目的通红,他定了定神,才看清夕阳西下。
灶膛里的火不知什么时候熄灭了,黑黢黢的一点余热也没有,等沉睡的知觉缓慢回到身体里,他感到手脚冰凉,而且麻木无力。
应该是不良睡姿导致的。他决定等这阵酸软感过去再起来。
身体不动,许远转着眼睛百无聊赖地看顶棚看天,眼睛转过某个位置,猛地停下来——郁风站在对面筒子楼二楼阳台上,跟他来了个四目相对。
许远愣了,不知道那小子在那里站了多久,如果没记错的话,自己刚才在梦里大呼小叫了吧,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叫出声来。想起自己在梦里屁滚尿流的样子,许远在心里骂了一句:操了。看郁风的眼神也变得不善起来。
突然,郁风用手指点了点自己脸颊,又指了下许远,嘴角还勾起来。
许远摸向自己脸,没摸出个所以然,上方郁风还是那副样子盯着他的脸。他想起屋里柱子上挂着面塑料镜子,扒着灶台沿从柴堆上爬起来,转到屋里去照镜子。
日了,喊没喊出来不知道,脸上居然有好几道黑白痕迹。大概是灶膛飘出的烟把他脸熏上一层黑灰,眼泪又在黑灰上冲出几条白道道。
不过郁风那是什么鸟眼居然这么远都能看见。
许远抽了塑料绳上晾着的洗脸巾在搪瓷盆里蘸蘸水,拧干把脸擦了一遍。他又去镜子面前站了站,确认脸上什么痕迹也没有了。
一股冷风溜着木门边缘吹进来,木门晃动着吱哑怪叫,许远连打了几个喷嚏,脑袋也跟着沉重起来。
郁风又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他以为许远很快会出来,毕竟这人就跟游魂一样,经常一个人在外面静悄悄地乱晃,似乎只有吃饭睡觉会回到瓦房里。
不过这次许远没有出来,马天才又跑到楼下喊他:“芋头!吃过晚饭没?出来打牌!”
“好。”郁风转身下楼,路过瓦房的时候朝里看了一眼,死静,黢黑,跟口棺材似的。
后面两天都没在街上见到许远,一个大活人突然没了动静让郁风隐隐有些不安,同时后知后觉想起来,那天看见他在柴堆上紧闭着眼又踢又打又哭活像犯了精神病,也许是真的想到什么过不去的事。那家伙不会是在屋里喝药死了吧?农村人喝药是报纸社会版的常客,每几个月就贡献一个丁点大的豆腐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