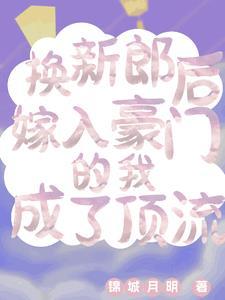风云小说>古玩宗师在现代TXT电子书免费 > 第27章(第1页)
第27章(第1页)
陈博彝见他似乎意动,十分高兴,马上滔滔不绝地介绍道:“主要是做瓷器,原先是找人介绍收购,但一来货源不能保证,二来偶尔会收到陪葬的明器,不成规矩。所以近来照我那几位老伙伴的建议,专门派了人到乡下去收购。你别说,还真淘换到了几样难得的物件。可惜的是农家不知这是古玩,有的当平常器物使用,有的丢给小孩子玩,难免磕着碰着,所以急需一位修复高手。”
打开了话匣,陈博彝喝了口茶润润嗓子,又说道:“不瞒你说,刚才我见你在那摊子上露了一手,就巴不得马上请你进店喝茶。但又没逮着机会,正琢磨着呢,可巧你过来问路,我一看,得,合该咱爷俩有缘份,赶紧把这番话统统说出来了。”
“哦,这么说,我这是自投罗网了。”雁游开了个玩笑。
“哈哈,我就怕我这地儿太小,留不住你这只冲霄鸟啊。”陈博彝半真半假地问道,“恕我多嘴:看你的手艺,必定是名师传授。却不知方不方便说说令师台甫?”
雁游早防着有人盘诘,已经编好了一套说辞:“小时候经常跟位邻居的老爷爷玩,这些都是他老人家教我的。当时说这些东西害得他十年不得安生,但没个传承又不安心,却又不愿再害了我,让我不要对外人讲。所以哪怕他去世之后,我也没对人提过半个字。我也是近来才知道,当初以为是玩的东西,竟是门难得的手艺。”
老一辈里有这样经历的人不少,陈博彝点了点头,毫无怀疑地接受了这个说法:“唉,这位老前辈也是生不逢时啊。”
雁游不欲在这上面说得太多,顿了一顿,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陈老先生,如果我到贵店工作,是什么模式呢?按伙计似的工钱加年底分红,还是单包论件计?”
“你竟连这些规矩也知道?看来那位老前辈教了你不少。”陈博彝惊叹地说道,随即又笑了起来:“不过如今是新时代了,咱们按新规矩来,你先听听中不中意:我每个月付你五十元的固定工资,你至少帮我修复五件东西。五件之外的,咱们再另行按照成交价的百分之十来提成,如何?”
这年头哪怕工作了十几二十年,有高级职称在身的人,工资也不过七八十元。对于雁游这个年纪的人来讲,陈博彝开出的价格可谓丰厚,哪怕是家境殷实的人,听了也不免动心。
所以,陈博彝几乎有九成的把握,相信雁游不会推辞。
孰料,雁游着眼的根本不是一时一刻的利益,他想得更远。
沉思片刻,他缓缓说道:“陈老先生,不如这样:我不要固定工资,每个月都按件给我计算。另外,我只负责接活儿修复,算是上门工作,其他时间我仍可做自己的事。如何?”
听了这话,陈博彝也在肚内暗暗盘算:不要底薪,听着反而是让自己省了钱。至于后一点,他聘请雁游,肯定是为了修复古玩,难不成还要让人家干店里的杂活儿不成?所以,上门还是固定工,区别也不大。
盘算明白,他爽快地说道:“行,就照你说的办。”
“那我先谢过陈老先生了。不过我还不能马上上班,还需要几天时间交接一下手头的工作。”
“没问题。”瞅着新挖到的人材,陈博彝笑得又添了几条皱纹。这时的他可不知道,用不了多久,他的开心就变成了懊恼。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数条街外,潘家园北门外的一家茶室内,慕容灰双腿高高架在桌上,一副散漫慵懒的样子。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隐在帽檐下的双眼里,透着多少不耐烦与厌倦。
对面的那对中年华夏裔男女若是知道他的心理活动,一定会气得尖叫掀桌。但他们现在很忙,忙着抱怨,忙着嫌弃。自打踏上大陆土地的那一刻起,他们十句话有七句都在贬低所见的一切,不停地比较褒贬,最后得出结论,还是米国好。
都怪这小子不省心,竟想背着长辈吃独食,否则他们也不必跟来受这份罪!这里的一切都差劲得令人发指,亏得这小子每天还悠哉游哉,一副如鱼得水的模样。
不过,若是为了那件东西,忍耐下恶劣的条件也是值得的。
一想到被自家门主默认的那个惊人传说,这对夫妇脸上重新露出笑容。两人对视一眼,男子打了个眼色,女子立即会意地开口:“阿灰,这次你爷爷让你回国,真是辛苦你了。如果我没记错,你的大学课程还没完成吧?耽误了学业可不好,不如这样,你把事情交给你四叔,我们留下来替你打理,你回米国继续念书吧。”
女子看似热心地劝说着,眼中精光不停闪烁:门派几十年都没让人回过华夏,这次老头突然派了最疼的小孙子回来,肯定和那个传说脱不了干系!如果能插手这件事,哪怕东西最后都要交到门派充公,只消中间截留几件,自己的小家可就几辈子受用不尽了。
思及私下里查找的资料里所描写的种种情形,女子简直恨不得上前猛摇慕容灰的肩膀,让他老实交待。
旁边男子的表情虽然没表现得那么猴急,但双眼中的灼热同样不亚于女子。
将这对精明市侩得过了头的夫妇神情尽收眼底,慕容灰在不耐烦之余,又另添了几分厌恶。
“四婶。”他不喜欢这个女人,自他她嫁进慕容家后,四叔就变得越来越不踏实,成天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无论如何,这是长辈,至少面子上要敷衍过去:“其实这件事上,爷爷一开始先问了四叔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