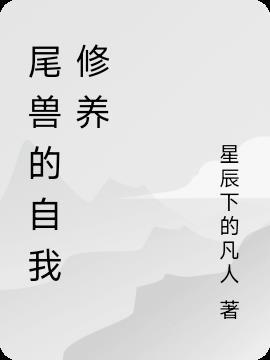风云小说>长兄骨科慕青全文免费阅读 > 第10章(第1页)
第10章(第1页)
她衣服有股清香,闻起来让人安心。
从此以后我记住了她,叫刘莹莹。
大概是从小没有怎么接受过来自女性的好意,除了姜灵韵,我妈——其实我记不太清我妈长什么样了,小时候她自杀走了,我就再没见过她。
她应该长得挺好看,我只能想起来她爱穿白色的衣服,头发长长的,不过我妈不爱拍照,一张照片也没留下。
不知道是不是基因遗传,从小穿衣服我就刻意地挑白色的,把头发留的很长,一直到腰际。
我的衣柜里白色的衣服最多,其次是蓝色,都是层层迭迭的洋装,系着精美的蝴蝶结,穿上好像小时候看的动漫里的魔法少女。
我哥肯定记得我妈,他应该是喜欢我妈的,我十六岁生日那天穿了长长的白裙子,头发散着,他看的愣了神,我吃蛋糕的时候他借口接电话出去抽了根烟,摩挲着我妈送他的手表红了眼眶。
我平常不爱完全把头发散下来,也不穿款式单一的长裙,一直长到脚踝。
披肩双马尾和蕾丝边睡衣这个造型才是我哥印象中的我,蹦蹦跳跳的下楼梯,穿着拖鞋吧哒吧哒跑到他跟前提着裙摆转个圈,笑嘻嘻地问他:“哥,我好看吗?”
所以哥看到我化了淡妆散头发的样子才会晃神。
你在想什么呢,哥哥?
在想我和妈妈真像,还是在想怎么突然妹妹这么大了?
我不知道,但我哥如果不说,就有他自己的理由。
很多事情他以为我不知道,其实我知道的可清楚了。
在卜盛辉的压迫之下长大,我学会了悄无声息的走路和把存在感降低到零,有时晚上穿着白裙子下楼,一点声响都没有,还会吓到家里的保姆阿姨。
我哥很多时候爱去天台抽烟,然后一个人偷偷红眼眶。
我没资格说我哥爱哭,因为我哭的比他还多,但我每次哭都有哥哄我,我哥没有,陪他的只有逐渐熄灭的烟蒂和天台上的冷风,还有往下眺望,满城的灯火。
天台是个好位置,我也爱去,站在那往下看,车子人群就像蚂蚁一样小,然后你就会发现狗屁挫折什么也不算,底下是满城人间烟火气,头上是冷冷的月亮,身处天地之间才发现自己这么这么渺小,或许只有灵魂的重量堪堪和宇宙比肩。
我有时候站在那思考人生,我哥上来了发现我在,就悄悄地下去。虽然都没开口说,但是心照不宣的,我们都没打扰对方思考这个年龄段的事情。
我和我哥差了八岁,按理来说,普通人家的兄妹俩一定是从小打到大,哥哥嫌妹妹烦人精,妹妹嫌哥哥神经病,而我们却默契的,巧合的,在我妈走后没发生任何矛盾,也不会有年纪大的一方说教另一方的情况出现。
哥没把自己当成什么可以随意质疑我的选择的人,也没把自己当成和我一样的愣头青,他很聪明,选择了一个微妙的境地。
或许他早就想通了,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就想通了,天地乾坤之间各有各的愁苦烦忧,除了自己谁也没法感同深受,什么安慰都太轻薄,显得无足轻重,不如放对方吹吹冷风看看夜景,想通是好事,想不通就去他妈,困了就去睡觉了。
我哥一直挺豁达,对于我的捣乱,他说累了就不搞了;对于我的叛逆,他说骂也没用,想开了自己就听话了;对于我的厌学,他说爱上不上,什么时候想上了和哥说一声,就行了。
其实有些事就这么简单,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因为屁大点事去把孩子搞的身心俱疲。
我自诩已经顿悟看破红尘,心里却知道离真正得道还远。
同年龄的孩子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大我的孩子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小我的就更不知道了,罢了罢了,每个人中二的方式都不一样,我又不是什么育儿专家,不提了,不想了。
扯远了,眼下最关紧的是我什么时候出院。
还有撞我的那个b货是谁。
我哥查到了一点,顺着这点蛛丝马迹摸过去,没想到摸到了本家。
好吧,其实也不是那么意外,仇家那么多自然有自家人。
古人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这话说的是一点毛病没有,我哥不是什么能行仁政的君主,自然有众叛亲离之事发生。
查查找找,找找问问,问问又查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哥相当记仇,势必要找出来谁动的手。
开面包车那人早找到了,奈何是个什么都不知道的替罪羊,局促不安的交代了,颠三倒四含糊其辞,最终一层一层顺着往上找才找到人。
替罪羊被我哥亲手送进了大牢,入狱前他突然大叫:“我也就为了那十万块钱!我还有老婆孩子!老婆得癌症了孩子才六岁!我能怎么办!对不住!”
他是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人,皮肤黝黑,想来是什么也不知道的苦命农民工,为了十万块钱把孩子的前程搭了进去。
也就为了那点钱。
他浑浊的眼球动了动,最后看向了站在我哥旁边的我,不知道在想什么。
可能在想小姐命就是好过贱民,也可能咒我和我哥不得好死。
犯了错就得受罚,法律不管你有什么苦难,一律进去。
这点毋庸置疑,但最后我哥还是心软,把那十万块钱留给了他孩子老婆。
我陪我哥一块去的,胳膊还打着石膏吊着,那替罪羊所说的老婆确实身患癌症,躺在病床上流泪,见我的时候泪流的更厉害,张嘴想说些什么,可能想说对不起,也可能想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