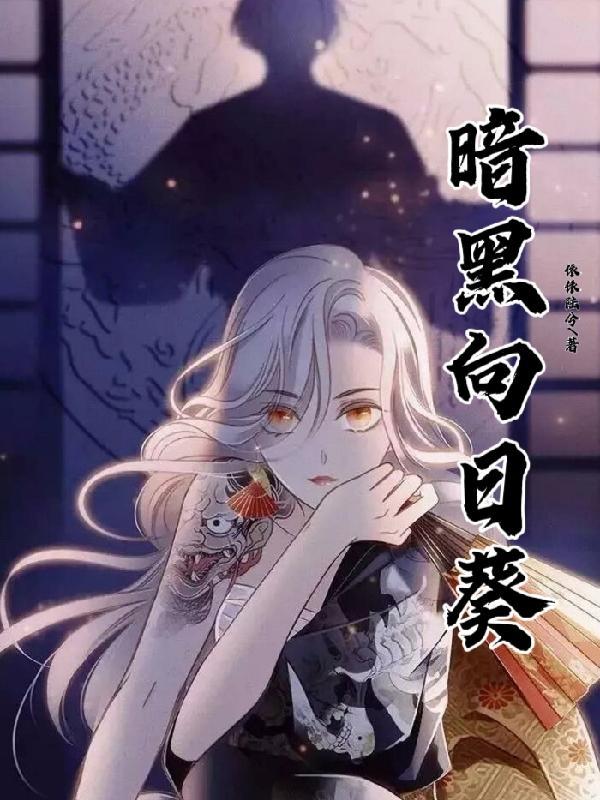风云小说>臣好看但想换个老板全文免费阅读 > 第40章(第2页)
第40章(第2页)
——皇帝果然将虚陇的副手王甘,交由左金吾卫收押。
现在王甘就关在白兆睿手底下,而白兆丰身为其弟,一定有机会接触得到,以往虚陇与白家泾渭分明,如今为了这个副手,倒是要和白兆丰说上几句话了。
虚陇在与白兆丰判断,却看到白兆丰对光渡微微行了一礼,并与虚陇拉开了距离。
这个动作,令虚陇面容有片刻扭曲,但是很快,他又露出了那种让人很不舒服的笑,“又见面了,光渡大人。我想我们未来数日内,还要再次见面的。”
“托陛下的福荫,还是别见为好。”
他将手伸入柜子最里面的位置,抽出了唯一一个不在任何归类里的画匣。
虚陇手底下的人,今日尤其老实,他们可还不至于忘记,虚统领几日前还受了陛下申饬和罚俸,连副统领王甘也折了进去,到现在都生死未卜。
“但我其实也好奇许久了。”光渡出其不意地问,“那位‘小宋娘子’,相貌果真与我有几分相似之处么?”
白兆丰一瞬震惊。
主座上的贵族青年,如转动一支毛笔般玩着手中的匕,指尖频频掠过寒光。
那是一段极好的时光。
画中着墨两人,其中一位锦衣少年身形瘦长,与一位女童牵手而行,那女童没有正脸,只有一个活泼的背影。
与光渡外貌相似,确实很有难度,而自己那夜的话,始终像一个蹩脚的借口。
这份沉默有些明显了,光渡都注意到了这位似乎打定主意,拒绝与他交谈的侍卫。
与此同时,中兴府。
光渡站住脚步,“虚统领,若你编排好了罪证,可以直接递御前,不用在这里诈来诈去的,太幼稚,没必要。”
那最要紧的想象,总会在关键处留下一片空白,如一团散逸于空中的铁水银花,片刻华丽后消逝无踪。
他抽开了装着光渡画卷的匣子,将那副画细心展开。
这位光渡大人,可不好惹。
火器厂的人走过中庭时,看到光渡站如定海神针一般,镇住了虚陇带来人的小心思,一时都有些扬眉吐气。
光渡大人早就交代了,火药来源一定是调查春华殿被毁一事的重点方向,这里既然是火器厂,就总归是避不开这一查。
药乜绗抽出画卷。
光渡下了马,牵着缰绳走过城中,以避免冲撞街道上的行人。
况且这次抽查,众工匠并不如何惊慌。
而白兆丰跟着光度,被迫在火器厂中庭的正中央,也客串了一次镇场子的驱邪像。
他暗自下定决心,只要是光渡说出来的事,必须要多几个心眼。
李元阙在空无一物的空气中,丈量着这位看不见的故人。
更别说光渡大人之前,早就都已经安排妥当了。
“怎么样?可有纺妹的消息?”
“下官最近派人在沙州走动。”虚陇突然开口,意味深长,“光渡大人,你以为自己,真的毫无破绽么?”
一座灯火通明的深重院落,最豪华的主房之中,迎来了新的变化。
他从不曾见过故人的面目。
“禀报族长。”下面的人低头汇报,“小姐……小姐在宫中遇刺。”
直到他们走了很久,天色已暗,中兴府亮起万千灯火,他们穿过中兴府的街道,来到白色的皇宫墙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