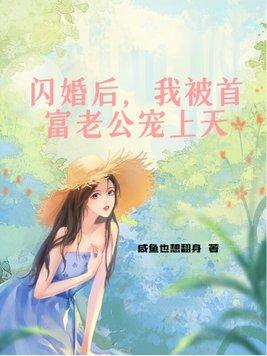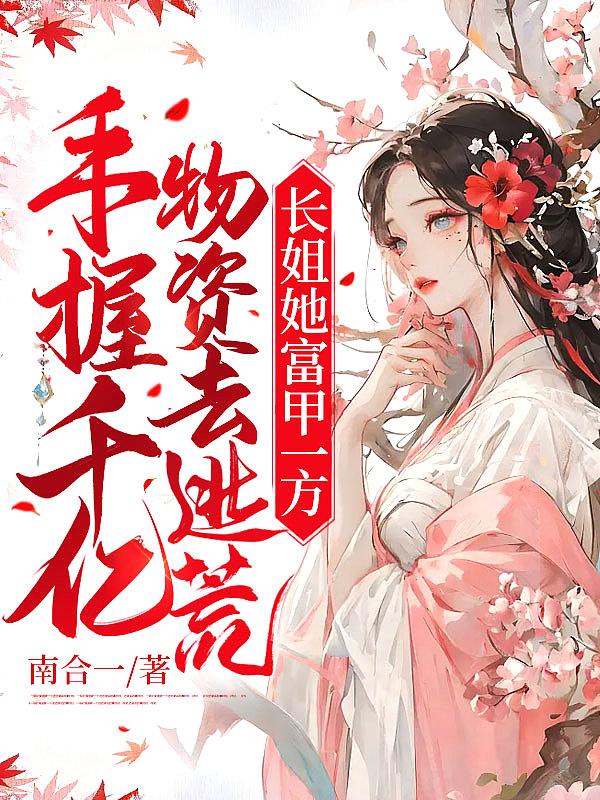风云小说>大不良是什么意思 > 第七章 人前显圣失败了(第3页)
第七章 人前显圣失败了(第3页)
那座巍峨恢弘的长安城再次出现,陇元镇仿佛凌空漂浮,俯瞰这座熙攘繁盛的长安城,他的脑袋一阵眩晕,视角随着老船夫的记忆不断变化:
他是江都府附近村子的渔民孙大曾,人生就像其他渔家平民一样普通——儿时生于蓬船中,老大商船讨生活,靠着漕运卸货、出海渔猎,日子虽然过的不富裕,但也算得上吃喝不愁有屋容身。
漕运开船不容易,贡物运到长安需要数月甚至一年,可以说是天高水远,可是,压船吏卒却都是从江都府附近挑选,船吏虽然是吏目,实际上跟服徭役没区别,官府不给银钱,只开具公验凭引,让沿途转运衙供给吃穿衣食。
不给钱、事情多、打点还要倒贴,这种苦差事一般人都不愿意干,这老船吏自然也不想干!
他本来也不想蹚这趟浑水,计划私下给官府使点银钱买个清闲,奈何家中妻子祖籍在关中,她思念故乡想让丈夫回去看看,一来二去,就没使这个银子,任由总督衙门征召他为船吏!
压船一年,回去时还可以给妻儿带点关中特产。
老船夫心中算盘打得啪啪响,却没料到,他自己,也是别人手中的算珠筹码。
正月十四,上元灯节前日,千家万户掌灯彩,渭河两畔笑宴宴。
老船吏跟其他年轻船吏一路吃着河鲜哼着歌,押漕船从潼关渡进渭河转运府,停在码头等待有司衙门查验。
他见渭河转运使陇世安出来,两人客套一番道句上元安康,又塞了几十两银子,吏卒心领神会赶紧检查完,盖了有司的印章准许放行,临了,陇世安还抓了一把贡橘。
等走远了,这老船吏暗自唾了一口,骂一句蠹虫。
漕船继续漂泊渭河,在渭南渡驿馆提了公验,从春明门渡入长安。
一入夜,两岸街灯明灭辉煌,这些船吏嫌弃开春风凉,早早进入船舱生起火盆取暖。
只听得咣当一声,船顶似乎有东西砸下来,漕船停在原地不再航行。
船吏都是渔猎人家,打小就听老辈说过河里怪事,什么河童河妖、水鬼水尸,听得耳朵眼都起茧子了。
这老船吏仗着年纪大,比年轻人多吃了几年盐,壮着胆子掀开船帘走出去。
刚才还洒满月光的船头甲板,不知什么时候沾满了河水,腥重味儿随风飘进鼻孔。
这老头还以为碰见了劫船水匪,眼见甲板空无一人,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
“呼!”
虚惊一场。
老船吏长出一口气,他收起长刀转身想回到船舱,这时,身后忽然刮来刺骨阴风,手里灯笼扑闪几下,随即被吹灭。
啪!
他的肩膀被人重重一拍,似有人出声:
“船家,借你东西一用!”
“何……何物!”
“项上人头。”
陇元镇回过神,蹲下看向这老船夫被拍过的肩膀,衣服上残留的气味儿,透着一股怪异。
古代制备火药的条件很落后,黑火药中木炭、硝石、硫磺中往往混有杂质,他能明显闻到火药中有股奇怪的味道,假如不是法医或者材料检验方面的专家,根本就无法嗅到掩藏在浓郁硫磺气息中的诡异奇香。
这气味儿,绝对是突破口!
他聚精会神,俯瞰着熙熙攘攘的长安城廓,以上帝视角打量着贡船的漕河路线。
从春明门到东市,只有一条漕河,经过放生池后,会从池子引出两条漕河,向北经过崇仁坊,向西穿过平康坊,这两个坊也有水漕贯通两地。
如果他是贼人,既然不在东市动手,一定是忌惮市署的检查,那么适合动手的,只剩下事故发生地崇仁坊,以及有漕河贯通的平康坊。
长安城只在上元节取消宵禁,这艘船是上元节前一日就进入长安,夜间若有动静,武侯、打更人、不良卫怎么也不会毫无察觉,除非……是坊内本来就热闹杂乱,贼人靠着这一点,掩护了自己的行动。
晚上,能无视宵禁昼夜喧闹。
坊内人多眼杂,三教九流都有。
不良人、打更人、武侯不仔细查。
河面船多喧闹,可供掩护。
陇元镇拍了一下脑门,他疯了似的打开舆图,目光注视着平康坊,嘴巴拉起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