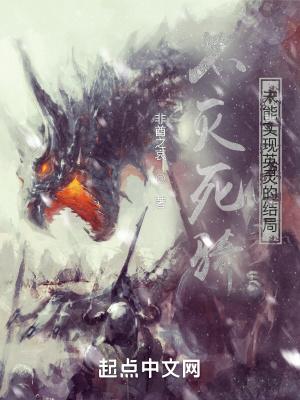风云小说>试谋未遂边棠资源 > 第15頁(第1页)
第15頁(第1页)
「大概一周以前,在醫院北邊5oo米的那條步行街那兒。」
「他做了什麼事讓你印象深刻?」
「……他叫我齊度。」
楊牧的筆尖頓住了一瞬,在光潔的紙面上留下了一滴刺眼的墨色。
沈渡津曾用名齊度,這是他在第三次接診沈渡津時知曉的,至於改名的初衷沈渡津始終不願意多說,隻言片語中楊牧只能猜到是因為他的父親齊德。
沈渡津繼續道:「他想包養我。」他將頭埋得很低,聲音也不大清楚,不知是因為聲波傳播的角度問題還是因為他本身音量就十分小。
「你答應他了?」
「當然沒有。」
楊牧微不可查的鬆了口氣。
「你喜歡他?」他問了一個有些唐突的問題,就像一條正在緩慢行進的路突然開出一個側枝。
「不可能。」沈渡津反應迅。
「我只是猜不透他的意圖,他像是想讓我重成為齊度,又像是想讓我作為齊度的替身待在他身邊,這多可笑是不是。」他邊說邊扯著嘴角露出一個苦澀的笑。
「我昨晚徹夜失眠,導火索是他凌晨時在家門口堵我。」沈渡津說完便像是被抽乾了體內僅存的一點力氣,雙手攏住頭部呈保護狀趴在桌上。
他苦於被齊度的故人糾纏,又苦於自己無法掙脫出那股名為齊度的漩渦。
在沈渡津的意識里,他已經與曾經的齊度毫無瓜葛,從前楊牧不會強迫沈渡津與齊度融為一體,他更樂於採用能使沈渡津敞開心扉的方式——齊度是齊度,沈渡津是沈渡津。
而今天不行了,他即將問出口的問題終究證明他們本就是一個人。
「既然他認識齊度,那你呢?你不記得他嗎?」這話乍一聽像病句,卻是楊牧能想到的最委婉的表達方式。
良久沈渡津終於從痛苦中稍微掙扎出來,他很認真地回憶著,最終還是無果:「……我想不起來了。」
沈渡津的失憶並不是毫無來由。他的重度抑鬱是經年累月的積累而造就出來的爆發點。那段昏暗無光、生不如死的日子裡他只有將自己與齊度完全割裂才能找到生存的平衡點。
再加之,在他患病之際正好有一種完全針對抑鬱症治療的藥研發上市,他是最早使用藥的那批人之一。藥療效好,副作用也大,用藥者會出現不同程度的記憶缺失現象。
沈渡津出現的記憶丟失現象尤其嚴重,以二十四歲為節點,越久遠的記憶便缺失越嚴重。這個藥似乎是偏愛他的童年記憶,進入訓犬師機構前經歷過的事情都模糊得不成片段。
他總用齊度沒朋友也不懂感情麻痹自己,事實卻是他缺失了那段對於齊度來說很重要的記憶而已。
「你依舊對那些記憶沒有印象嗎?」
沈渡津搖搖頭,由於個人體質差異,有的人在停藥之後記憶自然恢復,而有人則需要漫長的藥物作用消除時間,時長說不準,極有可能是一輩子都不會再想起來。沈渡津明顯是後者。
楊牧再次將不知解釋過多少次的失憶理由拿出來說:「你要知道,當時你選用的藥會對你的記憶進行無差別攻擊,不管是美好還是糟糕的回憶,都有被它抹掉的可能。」
沈渡津自嘲地笑道:「那我還真是不幸運,被抹掉的都是些可能還不錯的記憶,我父親對我做過的那些事卻還是一清二楚。」
「所以人要活在當下,對現在的你來說那些失去的記憶就如同曇花一現,但你往後的人生里還能看很多次曇花盛開。」
楊牧終於注意到沈渡津缺水發皺的嘴唇,走到飲水機前貼心的為他接了杯溫開水,「不用執著於那些不好的,那本就是不該留下的。」
沈渡津接過一次性杯抿了一口,異常糾結又執著道:「我永遠都忘不了。」
他不可能忘記齊德在他十四歲那年近乎綁架似的將他帶走,將他關入禁閉室里逼他屈服,不能忘記齊德完全背離人類道德的訓犬理論。那些往事就像惡刺一樣,沿骨而上,附骨而行,扎進血肉里。
楊牧:「那個人你打算怎麼辦?」
一次性塑料杯被沈渡津捏得變了形,發出細碎的響聲,他艱難地開口:「我不知道。」
訓犬師機構里有私人教師一對一上課,他從來沒接觸過正常環境裡的中學生活,也沒有過那些年少懵懂而生的愛意,更沒有愛慕者讓他實踐如何拒絕別人。因此面對突然闖進生活中的齊度的故人,他的第一反應是驚恐和逃避,緩過神來後又不知該如何應對。
他並不擅長規劃自己的人生,從前是被迫決定人生走向,等到決定權回到自己手裡時,他反而什麼都不會啦了。要是硬要找出一個值得活著的理由,那就是讓沈慧和沈俞過得更好。
沈渡津的「不知道」突然摁下了溝通的暫停鍵,診室里突然陷入一片安靜當中,只有牆上的掛鐘有節奏的走著秒。
楊牧思考良久:「這樣吧,換個角度思考,其實順其自然就很好,你不需要給予他過多的關注度,堅持你的立場,他會很快就淡忘你的存在。」
「畢竟他現在百般糾纏,或許只是在見到你以後激起了他內心深處對於齊度的記憶而已,等到他的興奮降到閾值以下,一切就會回到正軌。」
沈渡津病情並不穩定,楊牧思來想去也只是讓他保持現有狀態而已,過多的折騰反倒會適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