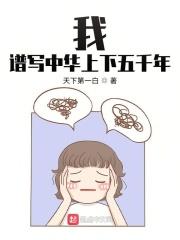风云小说>酒娘子花青素酒价格及图片 > 第7页(第1页)
第7页(第1页)
平日里村子里有大事儿,都会找里正做个见证。
外面的众人听到王里正都这么说了,便不再窃窃私语,等着族长和里正如何处理杜长和家里的事情。
杜老太爷刚才问过侄子,可侄子的话,显然不能服众,便问杨氏道:“大山媳妇啊,你好好说说,到底怎么了?你想怎么样?”
杨氏虚弱地站了起来,摸摸边上杜九妹的头,道:“大爷爷,大山走了,我们母子五人就任人磋磨,我是大人,打也罢,骂也罢,我能受得住,可八郎,九妹太小了。因为年纪小,不能干重活,整日被骂吃白饭。九妹的头,被婆婆打了流了很多血,到现在刚刚结疤,不相信您看!”
杨氏说着,扒开杜九妹的后脑勺。
后脑上枯黄的头发被剪掉了,上面赫然一一大块青紫,上面抹着一些叫不出名的草药。
“之前我以死相逼,才救下被卖的小九儿。婆婆就更加看我们不顺眼,趁着我们出去干活,用木板砸的。幸亏五郎回来拿种子,看到了倒在血泊里的小九儿,当时村里的李朗中给我们家小九儿拔掉伤口上的木刺,上了药,发了整整两天两夜的烧,才救回一条小命啊。”杨氏哽咽说道,越说越难过。
杜九娘知道现在该是她上场的时候了,火上浇点油,越烧越旺,她们三房才能得到最大好处,怯生生道;“太爷爷,别让祖母卖了我,我会好好干活的,不是吃白饭的;别让祖母逼我娘改嫁,我们已经没爹了,不能没有娘了;别让祖母送哥哥们去矿上,他们太小了,没力气,会死人的……”
短短的几句话,若是杨氏说,或许别人有几分怀疑,可杜九妹,从小不爱说话,被小孩子欺负只会哭,连告状都不会的一个笨丫头,今天却当着众人求族长,可见平日里杜婆子没少说这样的话。
众人的眼神看向杜长和,杜长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当初要卖了小九儿,他说了几句,但老婆子被银子扎了眼,根本不听他的话。
当时的的确确有人牙子来家里带人,村里人都知道,想否认也不行。
杜老太爷一听,这是想把大山的妻小,往死里磋磨啊。
大山那孩子为人仗义,哪家有事儿,都回去搭把手,又是打猎的能手,每年会给他送不少猎物,只是这小子运气不好,没能从战场上回来。
大山虽然不在了,但是得了大山好处的人还在,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山的妻小受苦受难。
“长和啊,既然你们容不下大山的妻小,那你们就分家吧。”杜老太爷能想到的完美解决之法,就是分家。
杜长和一愣,讷讷道:“我们……我们老的还没死呢,怎么能分家!”杜长和丢不起这人,若是这样把三房分出去,以后还不得被人戳脊梁骨啊。
杨富贵虽然希望女儿一家分出去,只是这话,他不好说出口,但杜氏的族长开口,那就不一样了。
“杜大伯,您一向慈悲,我杨富贵敬佩,全凭您做主。”杨富贵沉声道,语气沉重。
杜五郎今年十二岁了,这些天看着娘亲姐姐妹妹弟弟被人欺负,自己无能为力,非常难过痛心。
今天娘亲大闹,无非就是想让他们三房过得好一点。若只是口头上劝解,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状况。刚开始几天,或许会收敛;时间长了,他们定会固态萌生。
杜五郎跪在地上,给杜老太爷磕头,道:“太爷爷,我爹不在了,我就是三房的男丁。这些天我们每日起早贪黑干活,可却只能吃堂兄堂弟们一半的糊糊,所以才饿成这样。既然今天有太爷爷,里正爷爷做主,我杜家三房长子的身份顶门立户,分出去。以后我会好好干活,种地,孝顺娘亲,照顾姐姐妹妹和弟弟。”
胡搅蛮缠
平日里三房的孩子被欺负,吃的东西比其他人少,这些他都知道,只是不想跟老婆子闹,得过且过,没成想今日在这里丢了脸面。
“五郎,你说这话不是在剜爷爷的心吗?”杜长和难得说的一句完整的话,眯着眼睛看着杜五郎,暗示杜五郎收回刚才的话。
杜五郎今天准备豁出去了,又给杜长和磕了几个头,道:“爷爷,知道您心疼我们,只是我们在那个家没有地位,谁都能欺负我们,打骂我们。你能护得了我们一时,护不了我们一世。我爹已经没了,我是长子,应该像个男子汉一样撑起这个家,保护娘亲,姐姐,弟弟,妹妹。若是不孝,那都是孙儿一个人的不孝,您怪罪就怪罪我一个人吧。”
说完这些,杜五郎泣不成声。
弟弟还小,姐姐妹妹都是弱女子,现在这个时候,他们三房得有个男人站出来。父亲在的时候,父亲就像一棵大树一样为他们遮风挡雨。父亲不在了,他就是家里的大树,保护家人。
杜长和上前就要打杜五郎,但却被边上的杨富贵拉住了胳膊,道:“五郎这孩子懂事,说得合情合理,你凭什么打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们对我闺女,外孙子外孙女张口就骂,伸手就打,可想而知在家里是什么情况。杜大伯,今天我就做这个恶人,请求你把我闺女和外孙外孙女分出来,给他们一个活命的机会。”
杜老太爷刚才也看到杜长和伸出的手,面色不愉,沉声道:“栓子啊,你也糊涂啊!不想着给大山留个念想啊。”
杜婆子一愣,一听说要分家,顿时不乐意了,三房的这几个人吃得少,干得多,想怎么磋磨就怎么磋磨,这么容易指使的人怎么能分出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