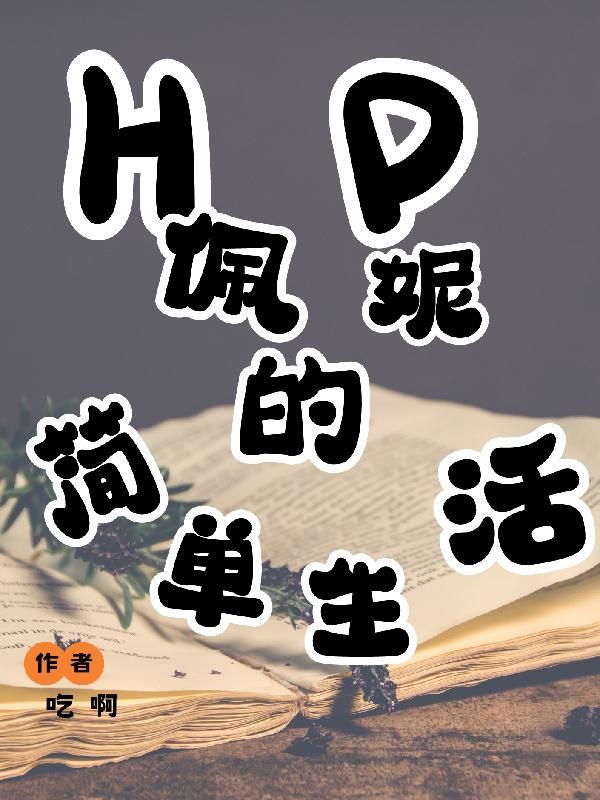风云小说>美女扶栏杆背影照片 > 第69章 入金陵(第2页)
第69章 入金陵(第2页)
皇甫明月眸中闪过暧昧之色,捏着帕子在嘴角处压了压,讥笑道,“你可别抬举她了,你又不是不知。。。。。。”
她又干笑了一声,略凑近了些,接着说道,“她一门心思闹着出宫只为找她那个情郎罢了,哦不,是她的那个亲哥哥。。。。。。”
说起来,五台山之事虽未成,却到底还是有些效用的,就是敲山震虎,要她怕,要她逃,最好逃到天边去。
文娉婷附和着笑了笑,想起幽禁中的李钰春来,“从前与李钰春交好时,便听她说过一些,我只当同门师兄妹,彼此爱慕倒也正常,没想到他们二人竟是兄妹,更没想到,云乐舒明知这层关系,却还执迷不悟地追了去,真是叫人匪夷所思。”
“要不然怎么说她是个疯子呢?真不愧是得过疯病的人。”皇甫明月止了笑,又道,“但也奇怪得很,李钰春不是与她势同水火吗,怎的这次竟豁出身家去帮她?也不怕祸及自己母家。”
文娉婷亦不理解,这两人平日里也没见得有什么往来。
“李钰春生辰那夜,我让芸清送了些助兴的酒过去,本想着促成君上与李钰春的好事,并就此挑拨一番,借机看看这两只猫儿打起架来,挠得彼此狼狈破相的惨状,可惜竟也没见着,还是便宜了那贱人。”皇甫明月说着,显出一副遗憾的样子来。
“话说回来,留得她这祸水在,终究是夜长梦多,若是哪天她又回来了,我们岂不是又要被她肆意轻贱了?姐姐。。。。。。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不若我们趁着她在宫外把她处置了罢?也免得君上荒怠朝政,日日悬心。”文娉婷两只似爪如钩的手五指张开,晾着将干未干的蔻丹汁水,鲜红的蔻丹像蛇信子一样攀在指尖,鲜红得有些骇人。
“既离了宫,也便碍不得我们的眼了,眼下君上横竖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也许过阵子便把她忘了,我们又何必脏了自个儿的手。”皇甫明月思忖片刻,才缓缓说道。
五台山腊梅林的事情她自知做得太过了,还牵连义兄被君上责罚,君上十之八九也知道是她在幕后主使,故而待她越冷漠,常常连敷衍都不愿,她不想再去触碰他的逆鳞。
况且云乐舒出了宫,茫茫人海,哪那么容易就能找到呢,只怕这辈子都回不来了。
即便到时找到了,她多年沐雨经霜、风餐露宿的,容颜早衰败了,怎还能像这样得君上青眼呢?她所依仗的也只有那一张脸罢了。
总之,此人是不足为惧了。
她若再对其赶尽杀绝被君上获悉,他们之间的关系只会雪上加霜,反而是顾此失彼,更加的不值当。
她还不如由现在开始经营好与君上的感情,她有父亲的鼎力支持,有皇甫一族的戎马功勋保底,她自己也生得不差,或许君上哪天也能宠她爱她,将她扶上后位呢。
“那便罢了。当务之急还是得找机会为大将军说些好话才是,他这些日子上了几道举荐的折子均被相爷驳回了,待君上回来,我们总得替大将军尽点绵薄之力才是。”文娉婷见皇甫明月不愿出面做恶人,遂不再多言。
皇甫明月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父亲近来愈热衷于植党结派,听闻还有京官偷偷前往西北拜谒之事,父亲不仅没有拒绝,还常常听信幕僚所言,做些逾制僭居的事儿,多少有些居功自傲了。
再这么下去,可怎么行?
她得送信去西北,好好劝劝父亲才行。
。。。。。。
在船上度过了漫长的三个多月,总算到了金陵地界。
云乐舒初到金陵头几日,就连绵下了好几日的雨,好不容易放了晴,天气已带了些暑热,真是“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一晃竟都四五月份了。
连云乐舒这么怕冷的,也穿不得那夹绒中衣了,才上了岸,便往成衣铺子去,另买了两身略薄些的圆领袍衫,又问掌柜要了些碎布,才找了个不起眼的客栈改造衣裳去了。
在船上这三个多月,她学着船老大和来往的男性客商们走路、谈吐,举手投足间,大致也能算是个男子了。
耳洞她也已经用粉盖住,就差这细肩细腰,一时半会她也吃不成个胖子,便只能在衣裳里面做点文章。
她笨拙地在衣裳内里腰部的位置缝了一圈碎布,肩部位置也垫了些,就连脚上的长靴也垫高了几分,如此一来,她这身形与原来相比便有了些出入,倒也能蒙混几成。
云乐舒缝完衣服,看着衣裳内部歪歪扭扭的针脚,又看了看手指上不小心戳出来的几个伤口,自叹自己的针黹女工实在是丢人现眼,见不得人,也不知道将来还能不能为师兄亲做一件衣裳了。
数着日子,若是顺利的话,再走两个多月便可从金陵沿东到达汴州。
只是她心里还是很担心,汴州那边把守森严,恐没有金陵这边风平浪静,她往金陵这一路,几乎是畅通无阻,甚至金陵城门守卫竟只是随机拦人排查,大部分的时候,来往之人皆出入自由,未见异样。
她也只能安慰自己,至少在金陵地界,能安生一段时日了。
自金陵南门入,需穿过几个县,方得以从东门出,到达汴州西门。
金陵地势平坦,据陵山以南,左靠邯临,北临榆关,因邯临、榆关地势多为山地,金陵倒像是被半围着的一片洼地,气候四季分明,春暖多变,夏雨集中。
金陵除了茶业繁荣外,矿藏也十分可观,煤、铁、铜、硫、磷、明矾、石灰岩等冶炼工业达。
因图璧京都远在珣阳,不便直辖,便由金陵本地官府依实况进行置点、设官并签户生产,但也仅限官府直营,禁止私人设冶矿洞、私炼器帑兵器等。
金陵气候适宜,地势又极利于种植水稻,原本农业也算达,本地农户居多。
但自频繁现矿藏后,君亦止事出从权,因地制宜将金陵划分为二,将农业种植统筹规整到西南方毗邻乾州沪西一带,气候地势差异不大,农户进行稻田耕作也并未受太大的影响,每年粮食产量的差额,便由其他主种植的地区补足。
而冶炼业兴起,最直观的收益便是每年课税额高达几万两白银的增项,以及因官营冶炼场产生的巨大用工潮,官府建冶炼场解决了大量流民、贫苦人家的生计,百姓纷纷转农为匠、工,投入道冶炼掘矿中,虽辛苦却能比从农时得到更多的工钱,且无需自负盈亏。
此举使得金陵的底层百姓皆乐于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