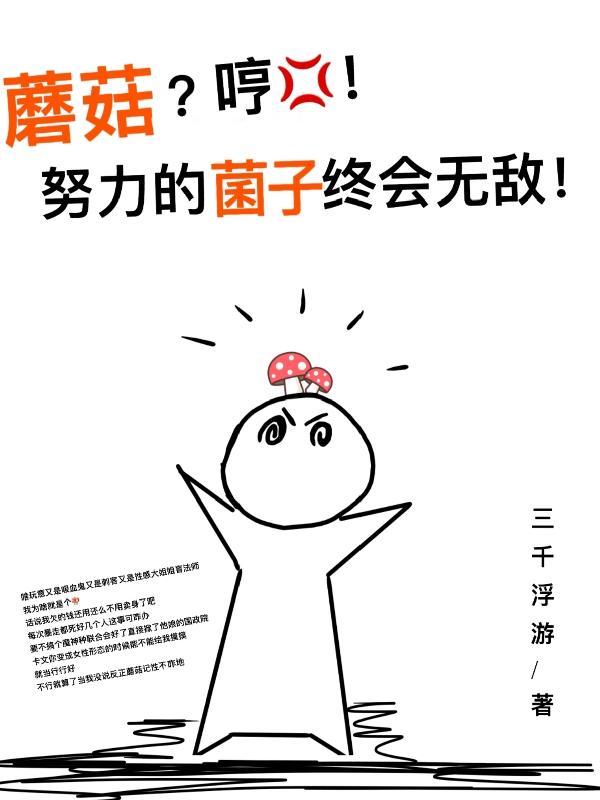风云小说>病重到已无法救治比喻人或事物无法挽救的地步 > 第90章 喜欢男孩还是女孩(第2页)
第90章 喜欢男孩还是女孩(第2页)
就好像在说:“这个破烂货怎么会被生下来。”
栀年假装自己看不懂,睁着又大又水的眼睛,怯生生地回望妈妈。
可从小的卑微讨好,她早就心思脆弱又敏感,她怎能看不懂。
她只是从来都在骗自己——
妈妈只是暂时不喜欢自己而已,她只要好好努力,把妈妈接出去,妈妈就不会这样对她了。
直到今天这一刻,她再也骗不了自己。
栀年从小就明白这个道理了,到现在更加深信不疑。
她明白,所有她在意的东西,到最后都会破碎不堪,被剥夺的一无所有。
她童年里唯一的救赎,子皓哥哥,最后被他的亲生父亲许强接回去,直到现在顾君弦认为她和许子皓有染。
她想好好守护的外婆,现在也寄人篱下,她甚至没有能力帮外婆渡过难关。
她,她真的好没用,好没用,好懦弱好懦弱……
可她也毫无办法,除了顺从面前的男人,她别无他法。
她心底那点挣扎,也渐渐没有了。
只有顺从,才,才是对的吧……
她心下酸涩不已,心疼的快无法呼吸。
原来,她那点尊严,真的很可笑。
她觉得自己是一个无比矛盾的人。
她一方面憧憬能靠自己创造出美好的未来生活,但一方面也从来不对未来抱有希望。
这种态度,对于她和顾君弦的喜欢,亦然。
她一方面憧憬他能对自己好,另一方面永远不敢靠近他,和他保持着得当的距离。
因为她知道,她们永远不可能。
这个男人在华国只手遮天,她害怕他还对子皓哥哥动手。
子皓哥哥是她童年唯一的救赎……
她紧紧闭上双眼,不想再让顾君弦看见她在流泪。
可仍止不住,这种眼泪更像是生理性的泪水,而非情绪崩溃的泪水。
栀年胡乱地摇着头,声音温软,带着浓浓的祈求,只希望能让男人别再生气:“对…对不起,对不起……”
男人非但没被哄好,反而怒气更甚。
他挑起她的下巴:“宝宝,别再跟我说,对、不、起。”
栀年一怔,睁开那双通红的兔子眼,对上男人阴鸷的眸子,心念一动。
满腹委屈与狐疑,被吞进肚子里。
栀年睁着又大又空洞的眼睛,不知道过了多久,纱帘不再摇晃。
她的身体也如同被拆散的架子,在他起身的那一刻,痛感向四肢百骸蔓延,吞噬了她最后的清醒。
*
“废物庸医,滚!”
男人低低怒吼,玻璃碎裂的声音从门外传来,依稀传入房内。
“顾先生,我们也……”
“滚!”
“是。”
一阵急促的收东西的声音,紧接着是急促的脚步声。
栀年头晕脑胀,泪眼朦胧地迷迷蒙蒙睁开双眼。眼皮却好像有千斤顶一般架着,掀起眼帘时无比费力。
她模模糊糊往上看着。
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一股莫名急促的心慌与恐惧又慢慢爬上心头,如同爬山虎一般,裹紧了她的心脏。
她,又被关起来了吗……
栀年意识到这一点,死死揪紧了被角。
她能感觉到身上的被子很厚,也应该很暖和的。
可她身体却冰的不像话,脚丫冻得像是冰块儿,可脑子却是又涨又热,又昏又沉重。
厚重的被子在她的身上没起到一点作用,反而压得她仿佛更喘不过气。
她终究耐不住脑子里升腾的一股倦意,眼皮渐渐阖上。
一池梦境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