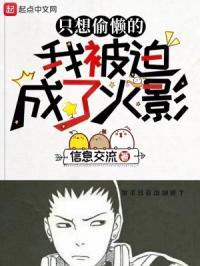风云小说>藏青果喉片的功效与作用 > 分卷阅读76(第2页)
分卷阅读76(第2页)
走出家,他对我和李译颇多指摘。当初只是以为他对我和李译较为严格而已。
他为什么上门,几个人怎么就突然开枪了。我神经紧绷,想着先杀了张明生,一切就能结束,没有看清场面,给在场某个人朝我放冷枪的机会。
为什么要杀我?
也许是我偏心,我总觉得朝我开枪的一定不是李译。
可老师终究是在小杨阿姨离开以后出现在我世界里的第一个没有血缘的亲人。
我不敢去想。
我是真的受老天垂怜重来一回了吗?
为什么我频频身体冷,仿佛下一秒魂魄就要跳出躯体似的。
那神棍讲我命不久矣是什么意思,他看出什么了吗?况且,我真的能让往事就这么如烟随风,然后重新开启新生活吗?
我想享受,又觉得自己在偷生。我想放下,又忍不住频频扑上去。
叹一口气,我翻过身,昏昏沉沉入睡。
第58章五十七
我在家估算年龄,知道张小元现在应该还是个小豆丁。但心理准备仍然在见到他的那一刻被击溃。一开始,在福利院众多熟与不熟的面孔里,我并没有找到他。我甚至开始怀疑,张明生是不是也在这个孩子的来历上撒了谎。
直到老院长放下手头工作,亲自来找我讲话。我与他的关系称不上多亲密。福利院太多孩子,来来走走,他看多了,也就看淡了,对孩子们只有最基础的关怀。我相信,他能为孩子挡在死亡之前,却没有余力再去填补这些孤儿内心的空洞。
他老了不少,头花白,不久就要退休了。我工作后便不常来,乍一看见他,也被他的衰老吓了一跳。彼此靠近时,我现他的手指时不时地着抖。早年他极钟爱书法,总是一个人静坐抄写,风雨不动。看他现在的样子,恐怕是再也拿不稳毛笔了。我心中一阵酸涩,却不敢叹出气来。
“阿潮来了,”老院长不是港岛本地人,口音也十分平实,听起来字字清晰铿锵,“好久不见你,怎么,年纪轻轻,就和我一样有白头了。”
我正笑着,听他这么一说,下意识转头,去寻走廊的穿戴镜照,微一歪头,就看到鬓边一缕银白。我伸手去摸,搓了两下,并未见那白色消失。不是偶然蹭上的,也不是光线所致,而是我真的白了几根头。
我还记得上一世,又或许,是梦里,李译曾替我拔掉过一根白头。那时我已三十多岁,心力绞竭,身体羸弱,有白头也是正常的。谁知道,一朝梦醒,我重新变成二十几岁的青年人,这白却毅然决然地跟着我。
我看着镜子里出光洁的表面。
我忽然现,指针不动了。
难道是坏了?
不知道这样还能不能卖钱。
我决定明天去福利院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找到张小元。算算年龄,他应该已经到福利院了。我打算给他买些礼物。
我不结婚,没有伴侣,收养不了小孩。
看来这辈子只能同他做好朋友,好兄弟。
我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困意侵袭,却忍不住去想:老师究竟是哪里来的钱买房子。
他有问题,我却无从查起。他和张明生父母的死究竟有没有关系,假如他捡到我丢失的证件,为什么不告诉我,而是留到许多年后示出,向李译证明我做了杀人犯的帮凶。
其实过去种种,我不是没有觉察出不对劲。
老师并不像他讲的那么云淡风轻。妻子低嫁,他背了许多年吃软饭的恶名,因此在家勤勤恳恳,做好丈夫好父亲。
走出家,他对我和李译颇多指摘。当初只是以为他对我和李译较为严格而已。
他为什么上门,几个人怎么就突然开枪了。我神经紧绷,想着先杀了张明生,一切就能结束,没有看清场面,给在场某个人朝我放冷枪的机会。
为什么要杀我?
也许是我偏心,我总觉得朝我开枪的一定不是李译。
可老师终究是在小杨阿姨离开以后出现在我世界里的第一个没有血缘的亲人。
我不敢去想。
我是真的受老天垂怜重来一回了吗?
为什么我频频身体冷,仿佛下一秒魂魄就要跳出躯体似的。
那神棍讲我命不久矣是什么意思,他看出什么了吗?况且,我真的能让往事就这么如烟随风,然后重新开启新生活吗?
我想享受,又觉得自己在偷生。我想放下,又忍不住频频扑上去。
叹一口气,我翻过身,昏昏沉沉入睡。
第58章五十七
我在家估算年龄,知道张小元现在应该还是个小豆丁。但心理准备仍然在见到他的那一刻被击溃。一开始,在福利院众多熟与不熟的面孔里,我并没有找到他。我甚至开始怀疑,张明生是不是也在这个孩子的来历上撒了谎。
直到老院长放下手头工作,亲自来找我讲话。我与他的关系称不上多亲密。福利院太多孩子,来来走走,他看多了,也就看淡了,对孩子们只有最基础的关怀。我相信,他能为孩子挡在死亡之前,却没有余力再去填补这些孤儿内心的空洞。
他老了不少,头花白,不久就要退休了。我工作后便不常来,乍一看见他,也被他的衰老吓了一跳。彼此靠近时,我现他的手指时不时地着抖。早年他极钟爱书法,总是一个人静坐抄写,风雨不动。看他现在的样子,恐怕是再也拿不稳毛笔了。我心中一阵酸涩,却不敢叹出气来。
“阿潮来了,”老院长不是港岛本地人,口音也十分平实,听起来字字清晰铿锵,“好久不见你,怎么,年纪轻轻,就和我一样有白头了。”
我正笑着,听他这么一说,下意识转头,去寻走廊的穿戴镜照,微一歪头,就看到鬓边一缕银白。我伸手去摸,搓了两下,并未见那白色消失。不是偶然蹭上的,也不是光线所致,而是我真的白了几根头。
我还记得上一世,又或许,是梦里,李译曾替我拔掉过一根白头。那时我已三十多岁,心力绞竭,身体羸弱,有白头也是正常的。谁知道,一朝梦醒,我重新变成二十几岁的青年人,这白却毅然决然地跟着我。
我看着镜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