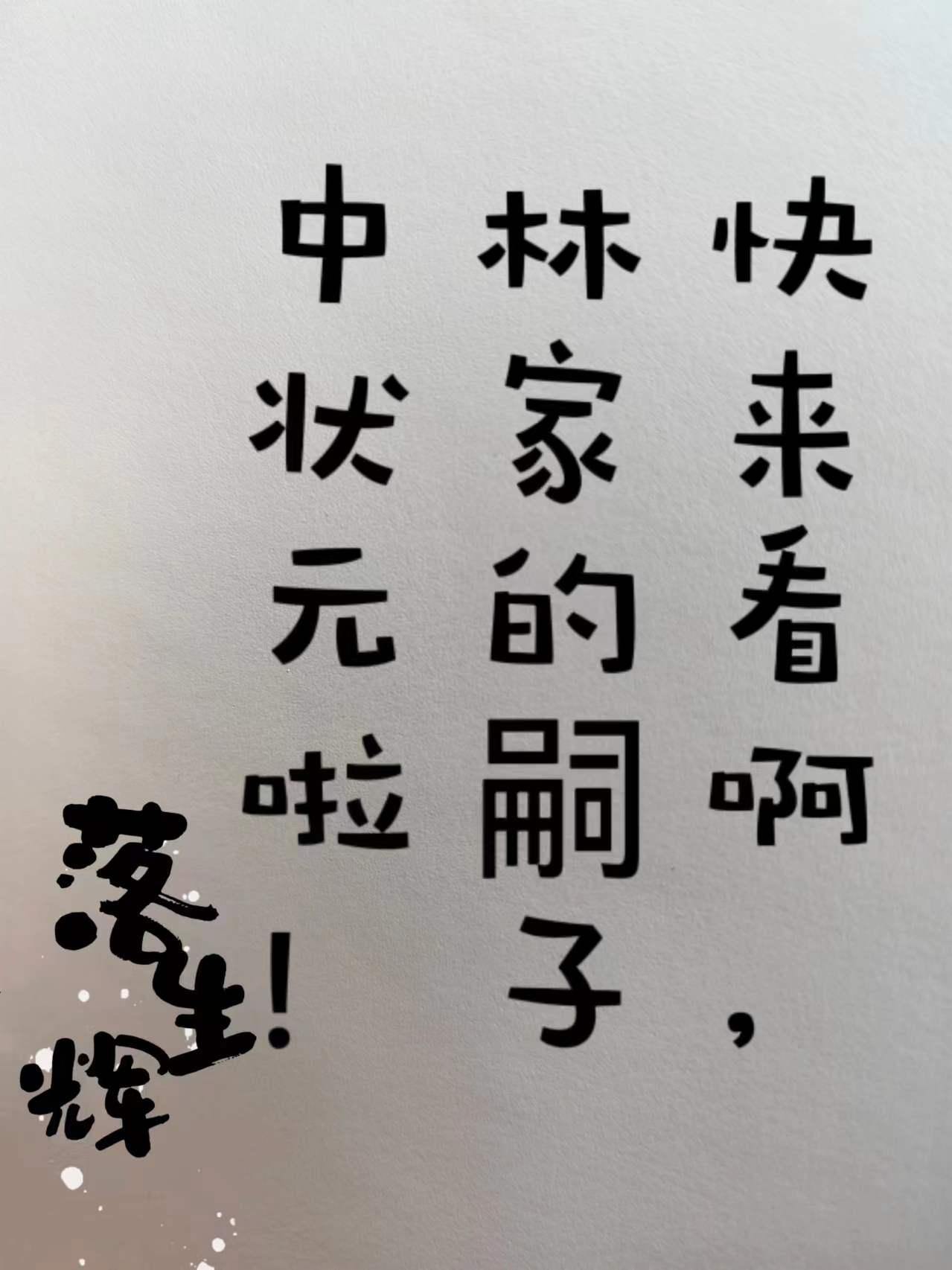风云小说>掌中娇裴寂 > 第五十六章(第1页)
第五十六章(第1页)
韦策站在库房门前,眼睛始终不离往内宫去的方向,心神不宁。
梁巍已经去了许久,始终没有消息,是没找到李肃,还是又出了别的岔子?
他等得有些心焦,由不得靠着墙,手指下意识地抠着墙上的砖缝,蓦地想到,这种背后告密的人,从前他是最厌憎的。
当初在国子监时,同窗之间难免会议论朝政,说起东市的铜匦时,有些同窗认为天子要想尽知下情,就不得不用些非常手段,铜匦的设立能让人心存敬畏,不敢为恶,而他一直认为,铜匦意在鼓励告密,长此以往,会令人心败坏,滋生奸邪。
为此,他还曾与意见不同的同窗舌辩数日,谁料想如今,他也成了告密之人。
韦策的手指用力抠着砖缝里的土灰,指腹磨得有些疼,心里的迟疑渐渐被压了下去。他要尽快爬上去,爬上去救她,太子纵容裴寂欺辱她,太子私下与外臣传递消息,是太子有错在先,怨不得他告密!
就在这时,梁巍急匆匆地走了回来。
一把将他拉进库房里,满面喜色地开了口:“韦兄,成了!”
韦策心里一紧,生出一股怪异复杂的情绪,闷闷问道:“怎么说?”
“李肃听我说了之后立刻让人跟了上去,你猜怎么着?”梁巍乐滋滋的,“不仅有杨家的下人,还有太子妃的长兄杨万仞!如今连圣人都惊动了,直接去了东宫!”
铜匦,告密,奸佞小人。韦策脑
海里不停地冒出这些词,心烦意乱,却还是竭力平静着神色,问道:“没想到事情闹得这么大。”
“可不是嘛!”梁巍眉飞色舞,“虽然李肃没来得及说什么,不过我有预感,肯定是大事,说不定那位要如愿以偿了!”
他嘿嘿地笑了起来,韦策心乱如麻,那位如何才算如愿以偿?拉下太子,推上纪王,储位更替吗?
韦策不由得瑟缩了一下,头一次意识到,这事情的后果,很可能是朝野震动——他居然在其中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
兴道坊崔府。
裴寂低声向崔白说道:“……你快些想法子与赵骠骑搭上话,内中的详情只有赵骠骑知道,千万要说服他赶在面圣之前给殿下递个消息,好歹让殿下知道该怎么回话。”
他来得太突然,说的状况又太严重,崔白到此时还有没完全理清楚思绪,皱着眉头边走边问道:“是谁传信给你的?难道那人没说宫里现在的情形吗?”
东宫出事的消息是裴适之传出来的,他身为神武帝的近身臣子,一旦被人得知私自传递消息,立刻就是灭门之灾。裴寂停顿一下,含糊了过去:“我自有门路。殿下半个多时辰前离开了公主府,至今却还没回宫,陛下正命人满城寻找,所幸我今天恰好也在公主府,殿下临走时我觉得不对,所以让郭锻悄悄跟着照应,只是如今也联络不上郭锻,到底也不知道殿下究竟去了
那里。子墨,殿下如今对宫里的情形全然不知,万一回去后说的话与圣人知道的对不上,那就棘手了,你千万求赵骠骑抢在前面,好歹提点殿下一二!”
崔白紧皱眉头,点了点头:“好,我去想办法!”
“我去寻英国公和刘公,请他们立刻进宫照应,”裴寂迈出门槛,翻身上马,“但愿一切顺利,否则……”
后面的话他没说,只加上一鞭,急急地奔了出去,崔白叹了口气,跟着也翻身上马,往皇城的方向赶去。
半晌,崔纨从书房走出来,望着裴寂的背影,向母亲卢氏说道:“阿娘,我听哥哥说,裴寂好像养着个外室?”
崔家有意结亲之后,也没有瞒着崔纨,是以今天听说裴寂寻上门来,崔纨便同着母亲躲在书房里,悄悄窥看。因着裴寂与崔白是多年好友,所以崔纨早就见过他,对他也算熟悉,只不过从前裴寂只是兄长的密友,如今突然成了可能的婚嫁对象,此时再看他,崔纨的观感自然跟从前不一样。
更何况前两天崔白特意跟她说了沈青葙的事,崔纨思忖着大约哥哥是不太赞同这桩亲事,故而此时也是思来想去,难以抉择。
“一个外室而已,不算什么大事,”卢氏并不在意,道,“若是定下了亲事,就跟他家里提一句,打发了就行,十七娘,但从人物来看,你觉得行不行?”
单论人物,崔纨其实是满意的,但有这么一
档子事,总让她觉得心里不痛快,微微嘟起了嘴:“我听哥哥说,裴寂似乎对那个外室很是放在心上,阿娘,我好端端的,做什么要找他?”
“真要是放在心上,就不会只是个外室。”卢氏拍拍她,以示安慰,“裴寂人物家世都是一等一,像他这个年龄,许多人连婢生子都弄出好几个了,他倒是从没传出来过这些事,无非一个外室,真要是成亲的话,把人打发走了就行,比婢妾更容易对付。况且裴家还有一个绝好的好处,他家家规定下,除非四十无子,否则是不能纳妾的,只这一条,你嫁过去以后,不知道省了多少心。”
“我还听说,长乐公主对他有意呢,”崔纨还是觉得不放心,道,“听哥哥平日里说起来,好像他也常跟公主走动,说不定他心里存着当驸马的念头呢!”
“长安的世家子弟有几个愿意做驸马?”卢氏笑道,“好端端的,要给公主做小伏低,不像是娶妻,倒像是入赘了!再说以公主的性子,真要是有意招他,早就定下了,你放心吧,这一桩肯定是不可能的。”
“那,”崔纨低着头,半晌才道,“阿娘,等我再问问哥哥,到时候再说吧。”
永兴坊中。
郭锻离去之后,杜忠思从后墙翻进酒家,又趁人不备跃上二楼,刚在郭锻定好的雅间里坐下没多久,外面突然一阵喧嚷,跟着又突然安静,杜忠思便知道,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