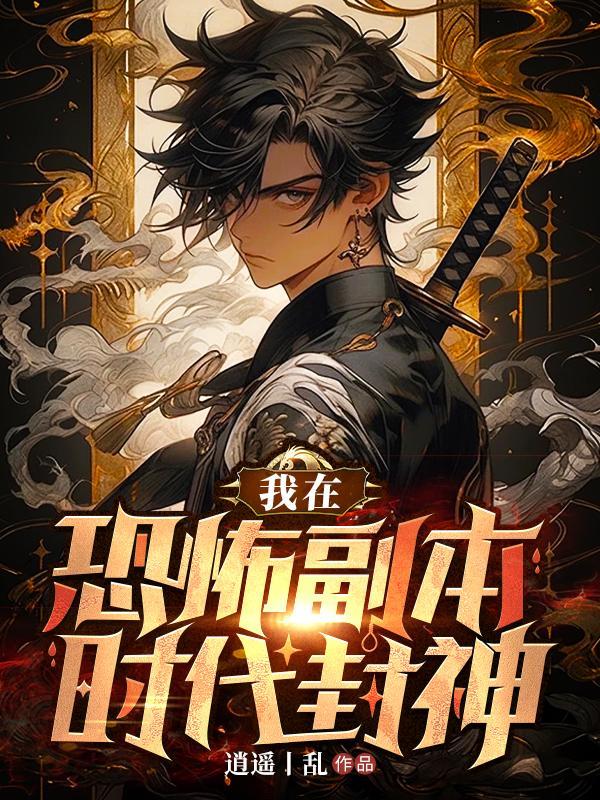风云小说>有才无德是 > 第142頁(第1页)
第142頁(第1页)
裴讓反過來勸慰他,說有這些就足夠了。
「反正以後的日子,是我們倆過。」
裴崢平時總仗著年長,把裴讓當小孩子照顧,但事實上裴讓在很多方面能反過來照顧他。
這樣挺好,畢竟裴崢也並不是無堅不摧。
*
從墓園回到市區,天色近晚。
裴讓提議說就在外邊吃,他想吃燒烤,期末考試結束和室友們約著吃燒烤沒吃盡興,帝都的物價過於離譜。
「本來我還想偷偷買單多一些的,結果被他倆發現了,硬是不要我請客。」裴讓嘟嘟囔囔。
「你那倆室友家教都不錯,肯定不會白占你便宜。」裴崢說,「你這四年處下來,或許會收穫到一生的朋友呢。」
但以後的事情誰能說得准呢,裴讓現在一門心思想吃燒烤。
他找了附近評價最好的燒烤店,給裴崢報了人均價格和店內的招牌菜,裴崢也沒有挑,說你喜歡就好。
「你到時候吃得少,我就不好了。」裴讓說。
「有粥就行,你不是說他們家招牌是黃鱔粥嘛,可以去試試。」裴崢說。
得到裴崢的保證,裴讓自覺地開始導航,穿過兩個路口,他們就經過了那家燒烤店的門口,裴崢又兜了個圈子找著車位,下車時離餐館還有段距離。
他倆旁若無人地手拉著手,行道上的榕樹在晚風裡枝葉搖曳,空氣中飄著燒烤的孜然味,那家燒烤店大開著店門,桌椅板凳在人行道上擺開老遠。
裴讓莫名覺得這一幕似曾相識,可能人的記憶里總是會保留一個這樣安寧的黃昏,之後的日子在和這樣的黃昏重逢時會倍感親近。
「我想起一個事兒。」裴崢說,背景音是車水馬龍的喧囂。
裴讓偏過頭去看他,橙黃的餘暉光斑映在他側臉。
「很早的時候我在路邊撿到個小孩兒,大概三歲吧,走丟了坐馬路邊哇哇地哭。」
「那時候我應該是從老宅里跑出來玩,但跑出來之後不知道玩什麼,從小到大我就是個無的人,結果在馬路邊上看見那小孩,決定給自己找點樂子,按照課本說的那樣,把小孩送回家。」
裴崢停了停,裴讓適時地問:「然後呢?」
「然後他說他走不動,我才發現他膝蓋有傷,乾脆把他整個抱了起來,畢竟才三歲嘛,人沒多大一點。」
「再然後我就被咬了,嘶,那小孩三歲,牙口真厲害。」
裴讓看著他心有餘悸的樣子直笑,笑著笑著又砸吧出了些不對勁,總覺得這場景也似曾相識。
「我為了安撫他,跟他學了哄小孩的童謠。」裴崢繼續說,「就是之前給你唱的那,挺活潑的一歌兒,但那小孩一邊哭一邊給我哼哼,我覺得還蠻好笑的。」
「所以你笑了,而且笑得很大聲。」裴讓自然而然地懟了他一句,說完自己也覺得好笑,「還好你最後給送回去了,不然人家指不定怎麼想你。」
「你又知道了?」裴崢狐疑地問。
「我就是知道。」裴讓說,「我很有可能就是……」
「嘖,這長得也不像啊。」裴崢停下腳步,上下打量他,「當時他還沒我腰高呢。」
「三歲能有你腰高,我現在應該可以去申請身高的吉尼斯紀錄了。」裴讓嘆了口氣,「之後你是不是抱著那小孩找到了他們家的小飯館,當時接過小孩的是一個中年婦女,嗓門挺大。」
「真的是你?」裴崢語氣又驚又喜。
「嗯。」裴讓拉著他緊走幾步,到了燒烤店門口,他們找了位置坐下,接過服務員遞來的菜單。
沒忙著勾畫菜品,裴讓說:「其實那個小飯館是我當時鄰居阿姨開的,你見到的中年婦女就應該是我阿姨。」
裴崢拎起桌上的茶壺,熟練地倒茶水給他們倆的餐具消毒,「我還以為那是你媽媽。」
「我媽和我生父,現在可以確定是生父了,畢竟我不是咱爸的親兒子,那會兒他們感情就不是很好,兩個人都不著家,在家裡也是吵架。」裴讓接過燙好的杯子,擺放到自己手邊,「鄰居阿姨看我可憐,那段時間總把我帶到店裡,等我媽他們回來再送我回家。」
「他們很能吵架,吵得附近住的大家都知道他倆感情不和,還根據他們吵架的內容,給我編造了百八十個身世。」
「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我五歲,我媽帶著我嫁進了裴家。」
*
他們對視了一眼,好半晌裴崢找回自己的聲音:「咱倆還挺有緣分的。」
「也不算,你不提起我都忘了還有這茬,後面就算見到你也沒想起來。」裴讓故作輕鬆地調侃,他把裴崢燙好的餐具擺放齊整,又叫來服務員把水盆收走。
裴崢給茶杯倒了水,給他圓了圓話:「你那會兒光顧著哭,估計都沒看清我的臉,當然我也沒看清你長啥樣,只記得是只尖牙利齒的小花貓。」
「這形容有些肉麻。」裴讓打了個哆嗦,他把菜單和鉛筆推了過來,「但可能真有緣分這種東西吧,讓你找到我,我找到你。」
「你找到我,我找到你,然後我倆在一起。」裴崢轉了下鉛筆,勾了菜單上的黃鱔粥和一系列海鮮牛羊肉,抬眼正對上裴讓專注的眼睛,那眼睛漂亮又乾淨,滿滿當當裝著一個他。
「裴崢,」裴讓叫了聲他的名字,「最後你還是帶我找到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