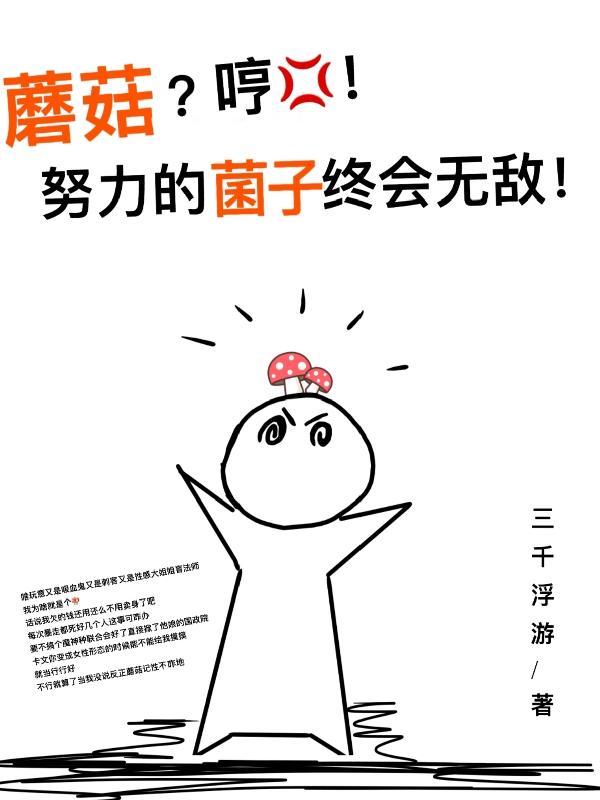风云小说>缨枝暮鼓笔趣阁 > 第29章(第1页)
第29章(第1页)
薄枝在小庙门口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副景象。
而与这座小庙的破败相比,裴怀瑾这白衣雪,金镶玉,看着真是格格不入。
她及时从门口离开,以免被他发现,而裴怀瑾挖着挖着,终于触到他想挖的东西,这是一坛酒。
男人将酒刨出来,轻轻揭开了酒封,经年陈酿的香气便从中散发了出来,他缓缓盖上盖子,抱着酒坛便往寺庙之后的树林中走去。
细雨已经将停,土壤松软,鞋靴一步一步迈上去,都能闻到土壤的气味,薄枝静静站在寺庙,亲眼看男人迈着不慌不忙的步子,惬意悠闲地去了的背影。
望着裴怀瑾这一串略为古怪的行为,薄枝心中的钩子已经被这个男人勾了起来,毕竟从她现有掌握的情报来看,他这已经完全超乎意料之外。
山间雨停,薄枝摘下了白色幕篱,一张脸也暴露于周围环境之中,已经有了冷意。
她继续跟了上去。
若小的山陵树林中,仅仅立着一抷黄土,风卷起黄土中掉落的残叶,席卷着来到了白色的袖边。
裴怀瑾抬手接过这片叶子,用石块将它压在了石碑上,他看着这座孤零零地墓碑,上面篆刻着方正筋骨的手书,“姬氏之墓”。
另有落笔“长子裴怀瑾题”。
姬氏是他母亲,而山阴是他母亲的故土。
裴怀瑾长身而立,一人一碑立在远处,背影竟有几分萧瑟。
薄枝在他身后不远处,所以并未看到墓碑上的题字,只是这样一个景,难免凄凉。
见此,她也该回了,裴怀瑾来祭奠故人,还特意装扮上了,显然这人在他心中举足轻重,但这便与她无关了。
人生来有衣食父母,也自然有心中重要之人,薄枝来此只是好奇,没有追根究底的欲望。
只是在她欲转身离开的剎那,薄枝还是顿了脚步。因她想父皇母后了。
褚姓是昭云皇姓,父皇与母后二人也琴瑟和鸣,年幼的褚枝不懂何为生死两茫茫,何为承生命之重,她天真、热意骄阳,是整个皇宫都捧着的存在,是父皇母后以及兄长用死的代价教她成长。
重要之人总是在失去之后才会懂有多么迷惘伤痛,薄枝也是如此。
她终究还是没走,找了颗枝繁叶茂的大树跳了上去隐藏起来,想看看这裴怀瑾究竟是对何人祭奠?
薄枝躺在树上,便这么慢悠悠地等。
墓碑之前,裴怀瑾已经打开了那坛香醇的酒,一部分祭洒在墓前,而后自己喝了一口。
他深邃的眉眼望着这块碑,陷入了过去的回忆。少时他曾与母亲同回外祖家,也就是是如今的山阴县来省亲。
他母亲姬凝是书香氏族之女,姬凝逝世前最想看的,便是他能成为流芳百世的文官。
时移世易,他没能以文拜官,而成了武将。
树上的薄枝望着下面静立的人,像是一动不动的雕像,她拽过树上的枝叶,辣手摧花般在手中亵玩,腿悠悠地荡了起来。
男人也没有久留,只见他将酒坛放下,便离开了。
薄枝见人走远,自己从树上跳了下来,轻轻走至那墓前,眼睛触及到上面的题字之人时,她才知道为何裴怀瑾要避开所有人来这儿了。
姬氏一族,曾因文狱一事被诛九族,而这墓下,埋葬的是裴家家主原配夫人的尸骨。
她本为女子,可以依仗夫家逃过一劫,奈何其性柔却骨刚,自诩绝婚,与家族同进退。奈何礼法不允,她无法接受父亡族灭,世间也没了她的消息。
这么多年,没人知晓姬夫人的具体下落,却不想她已经离世。
薄枝依据曾经调查的整个中洲史籍,与过去串联起来,才明白过来事件的脉络。
天色已晚,她也该回客栈了,薄枝缓缓转过腰身,绝佳的耳力却燃让她意识到空气中不同寻常的危险。
刀锋破空的声音旋转飞来,薄枝将头一偏,将将错过擦过脸颊的匕首,一缕发丝被破空斩断,匕首已然掉落,徒留青丝在空气中飘着下落。
她回头看,原已经走了的人却回来,裴怀瑾一张冷凝的面容上,黑漆漆的眼眸望着这边。
薄枝错愕。
本偷偷摸摸的行为被人戳破,她心有些发虚,更何况她还撞到了如此隐秘之事。
眼见裴怀瑾一步步向她逼近,身后是墓碑,身前是他,薄枝退无可退。
“呵呵,裴大人,巧啊。”
她悻悻笑道,徒留尴尬在脸颊。
裴怀瑾目光锁在她脸上,走到她的面前,面上无甚表情,却让人感觉头皮发麻。
薄枝已经许久没有体会这种感觉了,上一次如此体验还是她少时习武于悬崖走绳的摇晃感。
他面上已经没了那副守礼的样子,眼神肆意又赤裸,漆黑的眼眸深如寒潭。
裴怀瑾望着这个胆大包天地跟踪在他身后的薄枝,他有意拉拢“他”,所以对薄枝平日的不守规矩多了几分放纵,可这不代表“他”可以触碰他的私事与底线。
薄枝眼神挨不住这般如同将她扒光了般的注视,绞尽脑汁的在脑中搜寻脱困之法,她欲张口狡辩。
可下一刻,男人大力捏上了她的下颚提了起来,她嘴巴被捏的变形说不了话,向上提起的力道让她被迫地垫底脚尖。
大掌几近包住了她的小半张脸,力道大极,原本脸颊就不多的白嫩软肉被他捏的溢出的指缝。
她费劲力气扒拉他的手臂却螳臂当车,力量悬殊。
“呜~呜~呜?”她瞪大了眼睛望他,这狗男人想干嘛?
帮他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