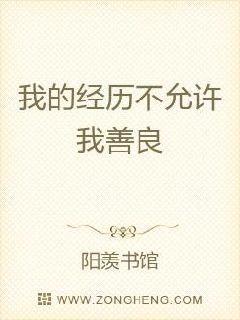风云小说>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意思 > 第65章(第3页)
第65章(第3页)
主仆两的一唱一和。
说的是她爱女之情,道的是她弃子之心。总归是一碗水端不平。如今长女更是开始听政论政,生生抢了幼子的道途。
谢琼琚把孩子握在床榻,眼见阿梧眼中的一点温情散开,只在榻畔坐下,边撩起他右边小腿,边道,“妾先有的皑皑,自然先和皑皑处着。那会学着抱她,没少让屋里的姑姑、嬷嬷们指导过,虽说有些经验,但多年来也手生了。近些日子,才又练了练,想着别摔了阿梧就好。
这会薛灵枢已经过来,彼此间的争锋便停了下来。
“夫人,我们先给小郎君施针,然后再行推拿。”薛灵枢走上前来,铺开药箱。
谢琼琚有些失神。
这是她头一回看见孩子的小腿。
因为肌肉的萎缩,内侧凹陷,存皮包骨却是没有半点余肉,只有左边正常小腿的十中之三粗细。
薛灵枢与她说过,孩子当初在她腹中时,横位而出,不得已已折断了他的右侧手臂和小腿。出生后接上臂膀,孩子已经奄奄一息,再试过接回小腿,孩子哪里还撑得住,便搁置了。后来周岁之后也普试过一回,没有成功。又因为早产根基太弱,各种风寒急症连番侵袭,故而心思都在养护他的元气根基上,小腿便一拖再拖,到了如今模样。
谢琼琚不知怎么偏转过头,目光凝在贺兰仆身上,凌厉又持久。
贺兰敏见多了她温厚柔软的一面,纵是针锋相对她也是绵里藏针的模样,从未撕破脸面。这会的一瞥,让她生出两分心惊。安嬷嬷更是不自觉往后退了一步。
她盯着贺兰敏,阿梧便盯着她。回眸的一刻,猝不及防对上孩子双目灼灼的眼神。
在无父无母的岁月里,在她再也解释不清楚的时光里,阿梧知道的是,他的父亲受他母亲蛊惑至深。在连医官都还没放弃他的境地里,欲先放弃他。
阿梧谢琼琚敛尽片刻前控制不住的尖锐锋芒,太多不知从何处开口的话终是化作她唇齿间这两个
字。
阿梧闻声,竟也退去一层寒色。
被人唤过无数次的两个字,在这一刻,从这个妇人口中吐出,他不知背后沧桑与委屈,就是依稀觉得不一样。
她总能盈泪而笑,笑意中打颤。
阿梧心中软下一角。然余光偏见从座榻起身的老妇轮廓,颤颤身影。
他目光沉沉落在谢琼琚身上。对,祖母说过。她就是这样惑着、霸着、占着他父亲。
“会有些疼,你忍一忍。”谢琼琚的心绪和思维到底快过孩子,这会已经回来正事上。嗓音里唯剩了冷静和平和。阿梧从她的眉眼,重新划向欲来未来的祖母身上。
红的眼,蹙的眉,捏着帕子指尖泛出灰白色,同她两登霜色呼应。这才是急他、爱他、忧他的模样。
孩童将眉眼压下,看面容平静的妇人。看她低眉敛神盯在自己小腿上。看因她、他才有的残缺身体。
这日她因何在次此处阿翁有事不能来,带走阿姊前往议事堂。
她惑着阿翁舍弃他,阿翁因她而偏爱阿姊。有个声音这样与他说。但仿若又不全是。
在主殿中,阿姊待他也很好,还让他常去。她说,你常来,去缠着阿翁对弈,烦死他。她说,“莫怕,本来也是陪我的时辰,我分给我阿弟又如何又不额外占他功夫”
“那你也能来陶庆堂寻我”想和阿姊在一起的,但是总去主殿祖母会伤心。“我不去”阿姊的秀眉扬得高高的,一下便回绝了他。
阿梧突然便有些烦躁。胸腔中憋闷,一颗心不上不下。拢在广袖中的手握紧了拳,又松开,再握紧。
银针入穴的一瞬,他久而无力、知觉甚微的小腿上一阵尖锐的痛意蔓延开来,惹的他一阵瑟缩。然却没有容他挣扎,薛灵枢的一只手有力地按住他大腿,捏过下一枚银针示范给谢琼琚看。
“先入外侧足阳明胃经的上巨虚和丰隆穴。”他下针极快,痛意上来又瞬间散开,之后再是内侧穴道,稍后夫人推拿的位置便也是这些穴位。
谢琼琚颔,在两炷香后针灸结束后,开始给阿梧推掌。
推拿比不得针灸,乃是绵长缓慢的功夫。
谢琼琚早早便将指甲磨平的手贴上孩子小腿,阿梧便不自觉
要缩回去。
不知是因为前头针灸沉积的疼痛,还是不欲被她触摸,亦或是心中百转千回的纠结。总之,阿梧觉得很难受。偏薛灵枢将他上半身按得那样紧,半点不由他动弹。
谢琼琚的指腹微凉,劲道却是十足,四指在外,拇指在穴,力气又重又钝。阿梧这会确定是疼痛了。只一个劲缩起来。
疼松开
“忍一忍,适应了便好。”薛灵枢安抚他。“阿梧”贺兰敏赶上来看他。“不行便算了”安嬷嬷帮腔。
“姑娘,您慢些。”竹青低低开口。
唯有谢琼琚低着头,无人看清她面色,亦无人能阻她动作。
阿梧抬起身子,看埋头无声的妇人。
这样痛,可她就不送手。
咬咬牙,他也能忍。
可是剧痛催人意志,让他不想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