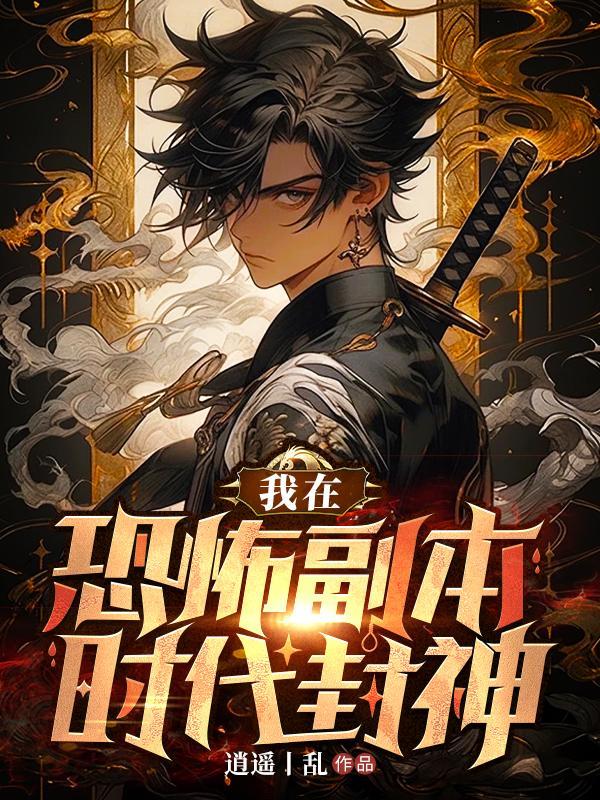风云小说>士兵突击袁许角逐60 > 第62章(第1页)
第62章(第1页)
许三多使劲点头:“嗯!”
两人坐了一夜火车,全程袁朗没有提任务,也没说带他去哪,只说会有人来接他俩,许三多真有种出来旅游的感觉了,如果算旅游的话,这可是他人生中头一遭。
在平泽西站下车后,他们在酒店住了一晚,第二天,许三多拉开窗帘,让阳光填满整间屋子,有种想要写信的冲动。
他想说,也许这会是一次很奇特的经历。
早晨,袁朗带他去早市上吃饭,这里是中国很北的地方,冻得蒸汽都结冰,可早市上熙熙攘攘,叫卖声、谈笑声不绝于耳,许三多像个孩子似的扭脑袋,袁朗向他介绍,这里人口构成复杂、文化特殊。
许三多问他怎么知道那么详细的,袁朗说,他曾经驻军在这里两年。
两人吃罢当地早饭,沿着路边散步,直到袁朗当着许三多的面接了个电话,简单地说了两句后挂掉,对许三多说:“他们来了。”
刚走到酒店,就见门口停了一辆车,见到二人走来发出一声高亢的鸣笛,许三多不能不注意它,这辆高大的、军绿色的吉普车。
转眼间,有人从车上跃下。
看到熟悉的脸,许三多在心里“咦”了一声。
是张扬,随后从副驾下来的是王冉,最后一个是楚成峰。
怎么是他们?
前往雪域
初次认识时情形仓促,这是许三多第一次仔细观察“来历不明”的三位军官。
打头的两个是王冉和楚成峰,楚成峰他是认得的,面容总是很严肃,看着有些凶,他身侧的那位军官脸型微圆,未语先笑,相较起来更和蔼可亲。
至于跟着两人后头的,不是张扬还能是谁?张扬像块不言不语的石头,留着不长的刺猬头,虽木着一张脸,但黑浓的眉毛像是时刻在拧着,难怪他有个刺头的外号。
袁、王、楚三个战友见面,简单地打了招呼,王冉滴溜溜的眼立刻落到许三多身上:“许三多!”
“您认识我?”
“那可不,百闻不如一见嘛。”
王冉心说,让袁朗和楚成峰争得不可开交的蓝颜祸水嘛,要不是他在中间斡旋,哥俩还不知道怎么解决呢?
他一把跨上来,手直接落到许三多肩膀上,捏捏这捏捏那,嘴里不时发出啧啧的声音。
许三多不知道怎么对待王冉的特殊招呼,自觉像一头瑟瑟发抖等待被宰的猪,幸亏袁朗及时制止,他才舒了口气,心有余悸地看着王冉。
王冉这才想到自己还没做自我介绍:“你好,你好,我叫王冉,你叫我冉哥就成。”
袁朗在一旁注解:“王组长。”
许三多行军礼:“王组长好。”
“哎好好好。”
袁朗又引着他看向楚成峰:“楚组长。”
许三多看向楚成峰,想起他们之间唯一那场谈话,几不可见地顿了一下:“楚组长好。”
楚成峰淡淡地“嗯”了一声。
张扬就不用介绍了,俩人交手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许三多从伍六一那学会“打出来的交情也是交情”,他对张扬友好地笑了笑,张扬似乎没意料他会给自己打招呼,眉间拧得更紧,别扭地对他点了点头,虽然看上去更显凶神恶煞。
基本的礼节完了之后,王冉建议大家吃顿饭,难得一聚,怎么着都得搓一顿,袁朗和楚成峰都答应了,他们到王冉推荐的一家饭馆吃饭,要了间包厢,菜很快上来,他们三个是领导,边谈边碰杯。
许三多不怎么习惯这种饭局的场合,低头专心吃他的饭,张扬也一样,滴酒未沾,埋头狠塞。
两人都是自甘寂寞的主,许三多吃了一会儿,注意到张扬光吃肉了,菜是一筷子也没动,便好心地说:“你要不要吃点菜,我们队的师傅说这样才营养均衡呢。”
张扬闷声道:“嗯。”然后默默夹了一筷子青菜。
许三多觉得他怪好玩的,真像702团部养的一只小狗,连囫囵着吃饭也像……咬着筷子想了一会,有点愧疚,哪有把人家比作小狗的?
另一边,王冉刚打开话匣子:“前段时间我去东部战区出差,你们猜我看见谁了?”
“谁?”
“咱们五班的乔思远。”五班是他们三个继新兵连后第一个服役的班。
袁朗想了想:“我有点印象,就是那个挺爱哭的小子,嘶,这都多少年了?”
楚成峰说:“十三四年了……他现在在做什么?”
王冉:“在信息化什么设备中心来着,大变样啊真是,你们想都不敢想,这家伙都秃了。”
袁朗被呛了下:“才多大啊他,我记得他那会头发也不少啊。”
王冉唏嘘不已:“要不就说吗?后来他不是分去高炮团了吗,一别这么多年,好好的一个青壮年怎么就秃了,老楚……你咋没反应啊。”
从旁听的许三多视角来看,楚组长真是个好人,因为他直截了当地说:“你管人家秃了没秃,管好你自己的头发吧。”
在袁朗的大笑中,王冉哀嚎一声,放下筷子,双手合十拜了拜:“黄天爷爷,厚土奶奶,基督耶稣阿弥陀佛,可别让我老王英年早秃啊。”
许三多:“……”
他还以为大佬们在一起会讨论什么重要又深远的话题呢,怎么还八卦人家脑门光不光呀。
谈完人家的脑门,王冉怀疑和乔思远家庭关系不和谐有关系,他们三个都是成了家的人,谈起家庭又是诸多唏嘘。
王冉扭过头对袁朗:“唉,谁不是稀里糊涂过来的,就算是你袁朗不也……”袁朗及时给他塞了一杯酒,王冉接过来咽了,含糊地说了一句,“哎呀,聪明人,聪明人我放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