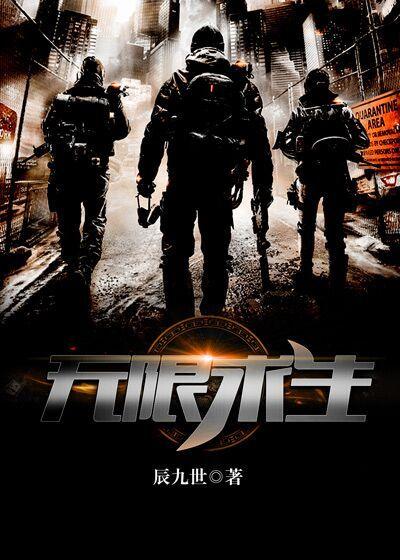风云小说>家有s鬼第十话 > 第6章(第1页)
第6章(第1页)
“嗯…忘了。”我耸耸肩,视线透过钢琴旁的窗户看出去,隔了一层玻璃,太阳和城市都被蒙上了一层阴影,光亮和刚刚进来之前一样光亮,但可能是空调冷气开得太足,我竟然感到一丝冷意,“鬼哥,你好了吗?我们要不抓紧?”
厉鬼翻了个白眼,一边抱怨着“还不是你动作慢”,一边消失在了我的视线里。
我把那个纸镯子拿起来,轻飘飘的镯子重了一点,我原本画上去的空花盆被填上了一层黑色。
纸镯子有了玉镯子的冰凉,仿若捂不热的冰凉。
--------------------
这是我第一次带着什么人来看我睡在病床上的爱人。
尽管这个人不是人,是鬼,还是厉鬼。
在电梯上的时候我推演了无数次厉鬼看到那具躺在床上的身体时会有什么反应,可推演的结果是人算不如天算,我在戴着纸镯子走进病房后,看见了一个坐在床边的背影。
别误会,当然不可能是我爱人醒了。
我打开门的动静让那个沉默的背影转过了头,像是每一次看见我一样,她和我打招呼。
“小齐,你今天也来啦。”
很稀疏平常的语气,我的手指忍不住去拨动纸镯子上垂下来的那根长长的线头,被磨损之后的丝线手感相当奇怪,我努力对她笑了笑:“好巧啊伯母,我这一周就来这么一次都碰见了。”
我还挺希望纸镯子里的厉鬼处在一个什么都听不见的状态的,毕竟当下这个场景里,我不用猜都能知道接下来她要说什么。
就像我想得一样,她开口了,说话之前先叹息着抚弄了一下手上的玉镯子——她知道我最受不了她这副样子。
“这是这周第几次?”
我不恨她,但偶尔,真的只是偶尔,很讨厌她这种多余的敏锐,特别是这种敏锐落在我身上的时候。
所以我装模作样:“瞧你说的,伯母,真的是这周第一次来。”
她又叹了一口气。
尽管我尊重她,但我猜她要说些什么我不爱听的话了。
“我很感谢你如此爱他。”
瞧,这哪有一个字我爱听。
“但是我们都知道,医生说手术后半年内如果没有醒来,小远苏醒的概率就基本等同于零了。”
“事情过去快两年了,我很感谢你一直守在他身边,但是小齐,趁着现在还年轻,你也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不能只围着小远转。伯母想小远一定也不希望看见你这样。”
她一直是一个好母亲,我知道,收养我爱人的时候她为了给他取名字上山求了佛,这才取来“净远”这两个字。
可恨她一生愿净远顺遂,偏净远落入尘埃,被丑陋的命运换走了善终的因果。
作为爱人的养母也罢,作为她自己也好,她都是一位相当仁厚的人,不怪罪谁,不迁怒谁,对我们一视同仁,甚至在现下的场景还在劝我放下虚无缥缈的希望,去过属于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