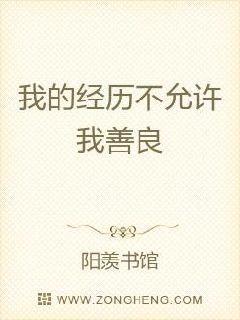风云小说>mr. 夏野 > 第72章(第1页)
第72章(第1页)
钢板房,也在下午的时候被全部拆掉了。
最后一天的行程依然匆忙。上午拍完收尾镜头之后,全体人员开始从山上陆续撤离,所有的设备及器材、个人用品统统搬走,临时的活动板房也将不再保留。
盖板房的时候用了不少天,全部拆掉只消一个下午。工人们三下五除二,就推倒了那些白森森的铁皮。几个月以来,作为拍摄中心的“中控室”、吃过很多次好吃的饭的“餐厅”、拥挤的“宿舍楼”,一夕之间,变成了一摊废墟。
村长齐振权带着村里的人来帮忙,随意地踩在这些拆掉的彩钢板上,然后又把那些好拿的钢板一片片带走,用来卖废品,回收价格可以有7块钱一斤。
郑南蕴看到后本来想说点什么,李卓曜摆摆手:“没事,让他们拿走吧。还能卖钱。”
齐振权把其中一摞钢板费劲地搬到自己的皮卡上,然后又殷勤的走过来对周楚澜说:“阿澜,我弄了不少废钢板,能卖不少钱。给你们家分一半,你到时候带回去。”
“谢了齐叔,我不好带,您都拿走吧。”
齐振权对他们家的态度也变了,之前没少找茬,暗地里使点绊子什么的,倒不是说这人多坏,纯粹是那幅嘴脸令人看了不爽罢了。如今却跟他们家亲近了起来,前两天还去他们家看他爸,说是这段时间活儿重,辛苦了,拎了三四十个土鸡蛋上门。
也无非是看在李卓曜的面子上而已。见自己跟一个名人关系好,便以为能捞到什么好处似的,拼了命地贴也要贴过来。
世态炎凉,周楚澜这些年没少见,对这样的事情也无甚在意,甚至冷眼旁观。
杀青宴上那些来敬酒的不也是,冲着李卓曜的名头来,热情一番后又迅速退场,不着痕迹。
李卓曜晚上醉的厉害,中途吐了好几次,吐完后才稍微清醒了点,结束后周楚澜架着他回到了酒店。
他一喝酒,情绪便会变得很亢奋,此刻也没到烂醉如泥的程度,剩余的一点理智全部转化成了某种兴致勃勃,脸色潮红,分享欲很高,拉着周楚澜就讲个不停。
“之前骂我的那个甜橙娱乐来采访我了,想笑,现在不骂了,个个都捧着……”
“杜导也来了,他也在贵州取景。就那个杜若风,拍纪录片很厉害的,他看了咱们样片说很喜欢……”
“薛晓茉,这几个女明星里面年纪最小那个,她跟我喝酒,喝一半问我有没有女朋友,我只好说,没有,然后她就说想当我的女朋友。我差点把酒洒她身上……”
周楚澜只是笑笑,没怎么说话,一边听他讲,一边帮他脱衣服。
“衣服脱了,味道好重。”
他们的衣服在地上凌乱地堆在一起,被周楚澜捡起来一块丢进了洗衣机里。
“你今天穿的黑色短袖,我穿的白色。还是不要一起洗吧,万一串色,把白衣服都染脏了。”李卓曜觑了一眼那堆衣服说。
周楚澜手指刚按上那个“start”的按钮,停顿了几秒,还是按了下去。
“没事,我的这件不褪色,不会把你的弄脏。”
他们的衣服和裤子,半黑半白地纠缠在了洗衣机里面,旋转着激出白色的泡沫,很快又溶于水里。周楚澜的黑色短袖已经穿了很久,久到再也褪不下色来,不会把李卓曜的白衣服染黑。
想了想,之前基本都在山上住,偶尔回家住的几次也都是匆忙。山上条件不好,衣服都是他都是给他手洗,两人的衣服按照色系分开。今天还是第一次用洗衣机把他们的放一块洗。周楚澜一直觉得,洗衣机是一件很亲密的机器,两人身上的衣服污渍都浸在一起,体味与汗味也在一起混合,不分彼此,然后在一圈圈的眩晕中被共同涤荡干净。
李卓曜进去洗澡了,刚洗一会儿又开着花洒,把浴室门推开,裸着身子探出来。
“进来一块洗吗?”
“不用,你先洗。我抽根烟。”
周楚澜站在窗前,点燃了一只烟,但是却没有吸,只是夹在指尖,看着它一点点燃为灰烬,棕褐色的烟叶变成了一粒粒的火星,燃起来的时候有过短暂的红艳,又在空气里迅速灭掉,终于成为一堆黑色的余烬。
李卓曜洗完后浴室空出来,周楚澜便接着进去洗,溽热的水雾充盈在整个空间里,置物架上放着的洗发水跟沐浴露,都是茉莉香型,淡绿色的瓶子上印着茉莉花的图案,外包装的slogan写的是:愿君莫离。
茉莉花的花语是“莫离”,被印在了这个系列的每款产品上。只是在那瓶沐浴露的瓶身上面,这行字已经褪到快要看不见了。
周楚澜打开花洒,拧到冷水的位置,照着头浇了下来,冷水浸过胸膛猛地一激,内心深处的某个想法渐渐上浮,清明一片,但又始终带着一层抹不去的哀和冷,像早春三月的几点微雨,淋在了刚泛出一点清冷绿意的草色里。
他湿着头发走出来的时候,李卓曜已经把衣服晾在了窗前,斜倚在床上等他。
“你明天收拾一下,后天下午跟我回广州吧。机票我买好了。”
李卓曜的想法是,周楚澜这几年都没出过独山县,他也想让他出去散散心。所以趁着自己这次节目录制结束要回台里,顺便带他去一次,到自己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看看。然后他们可以再慢慢商量以后怎么生活的问题。
见他爬上床,李卓曜便贴过来,熟练地钻进周楚澜的怀里。
“明天带你去看姜花吧,我家地里,这几天开的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