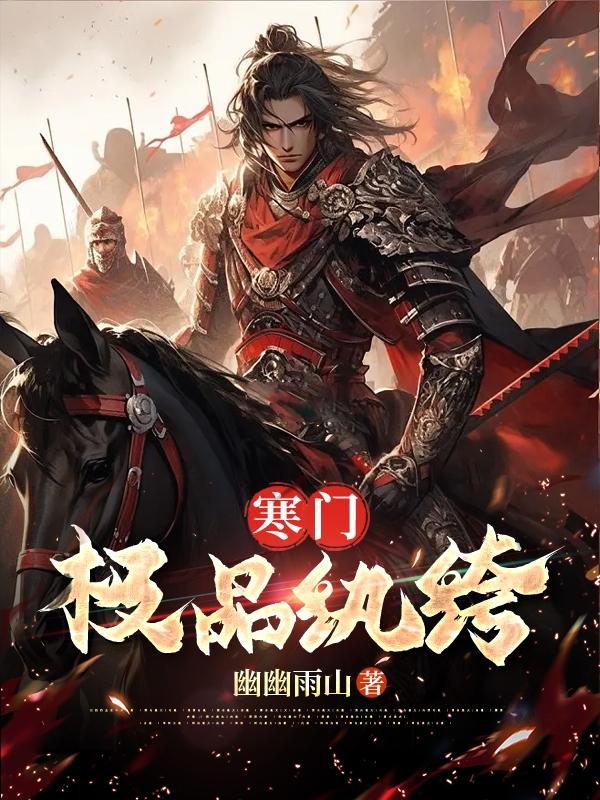风云小说>社畜恋爱法则兔美推荐 > 第8頁(第1页)
第8頁(第1页)
她的話沒有說完,七海建人就轉過臉,視線停留在她的臉上,「貓澤,我認為人際交往中,最重要的就是分寸感和距離感。」
「所以我不會對你多說什麼。」
貓澤飛鳥呆愣愣的望著他。
他頓了頓,繼續若無其事的說下去,「但是,我還是得提醒你……」
合著他還是看到了啊,貓澤飛鳥像個小學生一樣,站在原地低著頭,接受七海建人的說教,心中默默流淚,太宰治,你好有本事,我服了你。
只是,七海前輩,看別人手機屏幕,似乎也不是什麼有分寸感的行為?
「……以上,這只是我身為一個前輩對你的一點小小建議,聽不聽隨意。」
貓澤飛鳥小雞啄米般的點頭,迅抬起腳,正準備離開休息室,七海建人突然又開了口,
「等一下。」
貓澤飛鳥不解地回過頭來。
七海建人不太自在的抬手鬆了松領帶,緩慢的開口,「剛才是以公司前輩的身份對你說的話……」
「現在,以私人身份,我還有些話要和你說。」
第7章
七海建人能有什麼話要對她說呢?
該不會是來找她秋後算帳了吧?因為昨晚的事情?
貓澤飛鳥收回了搭在門把手上的手指,磨磨蹭蹭的回過身,低垂著頭,清潔的透光發亮的大理石地磚看起來冰冰涼的,模糊的倒映出她的模樣,和緩緩走近的七海建人的身影。
皮鞋踩踏大理石地磚,伴著有節奏的聲音,七海建人走到了她的面前,停在一步開外。
貓澤飛鳥感受到喉嚨有些發乾,下意識的緊張,已經錯失了打開門離開這裡的最佳時機,被七海建人叫停,二人獨處的這個房間,她這才微妙的體驗到危險感不停地迫近。
最先被打破的,就是合理的社交距離。
貓澤飛鳥聽著他的腳步聲停下,明明知道他站在面前,卻不敢抬頭。
這種感覺未免太奇怪了,她猶豫著想要抬頭,又像是什麼阻礙了她,以至於簡簡單單的動作,此刻卻怎麼樣也做不到,落在地面上的視線邊緣,是他筆挺的西裝褲腳與一塵不染的皮鞋,心臟砰砰的跳個不停,她也不知道自己在緊張些什麼。
這種距離,未免有些太近了吧,緊張到無法思考的時候,她就在腦中胡亂的想著這些東西,一步的距離,似乎已經遠遠地過了成年人的社交之間心照不宣的默契。
區別於遙遠的距離,她用眼角的餘光就能看見他的褲腳和皮鞋,捲起的襯衫袖口,露出的結實的小臂,自然的垂落在西裝褲邊的手腕上帶著機械石英表,與她手腕上帶著的秀氣的窄帶女士手錶區別分明。
這一瞬間她才懵然的有了屬於自己的領域被人強硬的踏入的自覺。
這是一個成年的男人,而他們之間的距離,模糊了界限,已經踏入了危險的區域。
這似乎與七海建人平日中給人的印象並不太一樣,嚴謹寡言、可靠的前輩,這並不是他的全部。
七海建人這個人給人留下的印象,都是在工作之中,雖然工作占據了他們生活的大半部分,然而人並不能只有一種東西組成,除了工作,仍舊有什麼,在他的身體裡封存著,昨晚,貓澤飛鳥就已經在那場混亂之中,隱隱約約的窺見了冰山一角。
那是不同於刻板印象的,對他這個人更加深入真切的認識。深入的,切身的體會。
除去普通社畜的這個表面。
他的內里,有著更加神秘和更加危險的存在,是剝去了寡言,尖銳的外殼,流淌在他的身體裡,深深地刻入本能的,不同於常人。
保持著嚴謹的同時,兼具的猛烈進攻性與血性的瘋狂,冷靜的掌控著全局。
七海建人會對她說什麼呢?
肯定是要說昨晚的事情了吧,都是她的錯,如果她率先道歉,這件事情可以當做沒有發生過嗎?
可是看七海建人這個架勢,這事情沒這麼簡單就結束。
酒精上頭,□□薰心,如果她能撐過今天,她發誓從此戒色戒酒,四大皆空。
如果不是因為這些世俗的欲望,她也不會陷入現在這種可怕的局面。
貓澤飛鳥大腦空空,隔著一層衣服,傳來門把手冰涼的觸感,但是此刻卻沒有辦法打開這扇門像往常一樣走出去。
她夾在七海建人和門之間的陰影的縫隙之中,屏住了呼吸,不由自主的緊張起來。
「貓澤。」
長久的安靜之後,七海建人終於率先開了口,貓澤飛鳥被他突然開口的低沉聲音嚇得一個激靈,終於來了,不管七海建人想要說什麼,說清楚也好,總比讓她一直處於這種惶惶的狀態中要好,總歸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早死早生。
她這樣努力的不停在心裡開解自己,終於壓下了強烈的心虛感,變得不再那麼緊張了。
她在心中深吸兩口氣,正準備抬起眼,一隻手伸到了她的面前。
那是她剛剛視線無處安放時,一直盯著的手,比她的手要大上許多,骨節分明,蒼白卻有力,手腕上帶著顯眼的銀色腕錶,此刻這隻手伸到她的面前。
他掌心的紋路很深,攤開的手掌上放著兩枚白色的藥丸。
作者有話要說:
我的腦中畫面
七海:來,大郎,吃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