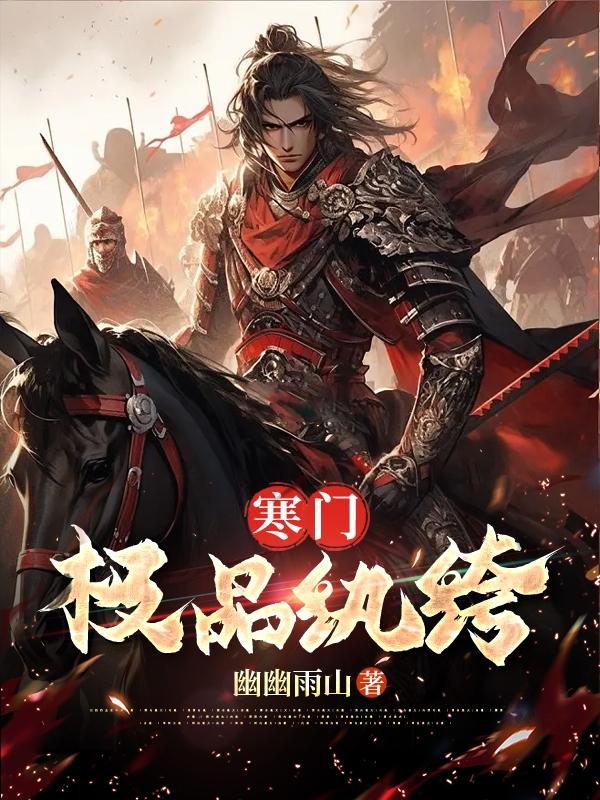风云小说>社畜恋爱法则 > 第15頁(第1页)
第15頁(第1页)
宏偉的高樓就像是矗立在城市中的鋼筋野獸,樓的下方就是寬敞的馬路,都被大樓投下的陰影覆蓋著,遠處的紅綠燈不停閃爍,伴隨著近近遠遠的車鈴聲。
遠近車燈,人群擁擠,而貓澤飛鳥只一眼,就看見了在人群中的太宰治。
並不是因為人群中,他的身姿和臉最顯眼,也並不光只是因為他們從小一塊長大,太宰治她再在熟悉不過。
貓澤飛鳥站在大樓入口處的旋轉玻璃門處,隔著玻璃遠遠地看向太宰治,太宰治就察覺到她的目光,將遙遠的投向空中,不知注視著虛無中的何物的眼神轉向了她,緩慢而輕的勾起唇角,露出了一個極淡的微笑。
貓澤飛鳥等待著如同風車的旋轉門轉向她,穿過了這扇玻璃門,走向了太宰治。
不論身處什麼樣的喧鬧繁華之中,太宰治總是格格不入,擁擠熱鬧的人群,鋪著瀝青的寬廣馬路,色彩鮮艷的車燈,倒映在他鳶色的眼中都變為一片空白,就像是現在,他仰著頭看著什麼,大樓投下的陰影也淡淡的覆蓋在他的身上,將他眼中的世界暈染成一片模糊不清的淡灰。
要說貓澤飛鳥為什麼能夠一眼就看到他,只因為這些匆匆走過的行人,喧鬧的城市,這個城市都是真實而熱鬧的,是五顏六色的鮮活存在,只有太宰治一個人,是寂靜無聲的,孤獨的黑白。
十幾年前他就是那樣。
貓澤飛鳥的腦海中,陳舊的記憶混沌的顯現,回憶起那扇大宅,鼻腔里似乎都又出現了濕漉漉的梅雨氣息。
記憶中,那扇一成不變的描繪著鮮紅的楓葉,撒著金粉的紙拉門。
小的時候的太宰治就站在那扇門後,一動不動,用幽深而空洞的目光注視外面盛開的紅櫻花,那因為睫毛濃密而纖長顯得幽深了的鳶色眼睛,就像是隔著一層薄薄的玻璃,注視著外面的世界,而他被隔絕在另外一側,就和現在一模一樣。
貓澤飛鳥抓緊手裡的袋子,加快度。
「在看什麼呢?」
她啪嗒啪嗒的踩著皮鞋,走到太宰治的肩側,學著他的樣子也抬起頭,一片片的玻璃窗倒映著落日,明亮亮的,十分晃眼,她只看了兩眼忍不住拼命眨眼。
好刺眼,正好被陽光照了個正著,眼淚都要流下來了,貓澤飛鳥正用手揉揉眼睛,就聽見耳邊傳來拉長了尾音,帶著淡淡笑意的聲音,「小香,你也想做伊卡洛斯嗎?」
「什麼?」貓澤飛鳥下意識地反問。
「人類,是沒有辦法接近太陽,觸摸陽光的哦。」太宰治轉過身,看向她,虛虛的圈住她的手腕,將她揉眼睛的手移開,「不然就會像伊卡洛斯一樣,蠟做的翅膀最終會被炙熱的陽光融化。」
「越是嚮往,越是接近,就越容易融化,最終粘住翅膀的蠟全部融化,從高空墜落,摔得粉身碎骨。」
「人類這種生物就是這樣,越是不該觸摸的東西越是想去觸碰,越是不可能的夢越是想要實現,為此不擇手段,不惜犧牲一切,真是可怕。」他微笑著將纏繞著繃帶的食指放在唇邊,「我的話,一開始就不會試圖觸摸太陽哦。」
貓澤飛鳥呆呆的說,「完全聽不懂,你如果不想回答我的問題可以直說。」
「啊呀,被你發現了?」他微笑起來,隨著歪頭的動作,微卷的黑色碎發柔順的向另一邊散開,「我只是在看這棟樓而已,好高啊,真是了不起。」
太宰治說完就轉過身去,即使炎熱的夏天他也穿著米白色的風衣,暴露在外的肌膚全都嚴嚴實實的裹著繃帶,長長的風衣擺在空中划過一道弧度,他伸出手從口袋裡掏出車鑰匙,上下拋著玩。
雖然是笑著說這句話的,但是卻絲毫沒有笑意,貓澤飛鳥看著他轉身的背影,心中微動,她原先聽太宰治身邊的人抱怨過他,也曾經聽說過他難以揣摩,心思深沉的傳言。
但是,太宰治說的是真話還是謊言,她卻可以僅憑著本能就準確的判斷,他是高興還是不高興,也都瞞不過她的眼睛。
不管成長成什麼樣子的大人,成為了別人眼中什麼樣的存在,在貓澤飛鳥心中,他永遠是那個牽著她的衣擺的瘦弱男孩,和那個時候一樣,是神一樣的好孩子。
貓澤飛鳥抓了抓頭髮,突然雙手一拍,「你剛剛在看這棟樓吧,說到樓,我想到一個恐怖的故事!」
「嗯?」
眼見太宰治被她的話吸引了,貓澤飛鳥得意的笑了笑,裝模作樣的咳嗽兩聲,「很恐怖哦,不要被嚇的睡不著覺,說有一天晚上,我一個人在家辦公,累了起來走走,走到窗邊時,你猜怎麼?我隨意往下一看,特別暗的街燈下面,有個男人,正提著刀捅人,血濺得到處都是。好嚇人啊。」
「我被嚇傻了,一動不動,殺人犯正好抬起頭,一下子看到我,我跟他的視線對上了,看著他濺滿了血的臉上慢慢露出一個笑容,然後伸出手指了指我,指了好幾下,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半天弄不明白……」
「他在數數吧?」沒等貓澤飛鳥說完,太宰治就興味索然的回答,他先將車門打開後才轉過身,微微彎下腰,湊近貓澤飛鳥的耳邊,壓低聲音,「1,2,3,4……4,馬上就來找你……」
「嗚哇。別嚇我啊!」貓澤飛鳥背上一涼,一把將他推到一邊。
「哈哈哈,小香,明明是自己說的故事,還能把自己嚇到的,這個世界上只有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