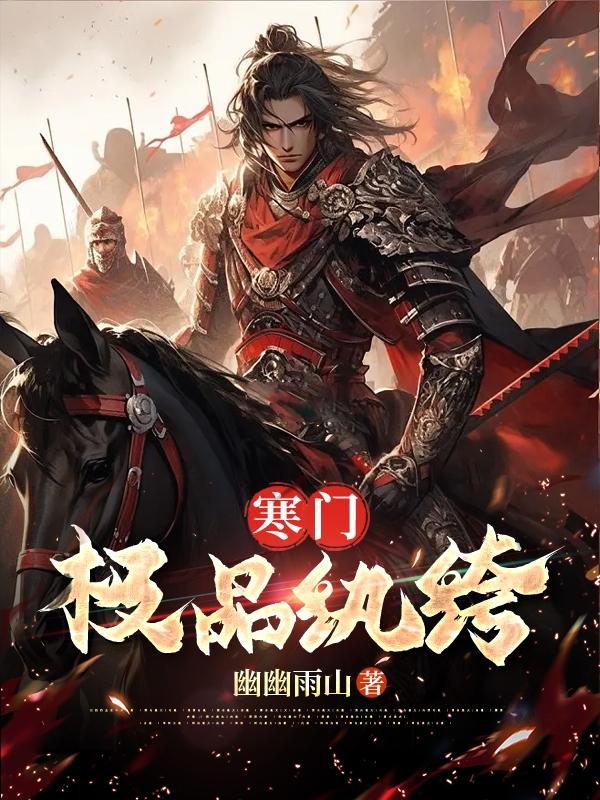风云小说>作为劳模的糟心哥哥txt > 第101章(第1页)
第101章(第1页)
羽生纪泽关上门,问道:“爬这么高?”
桑名真有些头疼:“一不留神就自己上去了,它还以为像是家里能跑酷呢,上去了还自己不敢下来。”
一人一猫在这里僵持了有一会儿了。
桑名真主动将位置给羽生纪泽让开,催促道:“我上不去,你应该可以,帮我把大福带下来。”
羽生纪泽抬头估算了一下距离,然后找了个地方垫脚往上跳,让一只手攀上书架顶,发力弓起手臂,用空余的手将金吉拉抱了起来,随后才轻盈落地,将乱跑的猫放在地毯上。
高兴的金吉拉使劲儿拿脑袋蹭蹭他,叫声一声比一声娇软。
桑名真板着脸教训猫,也不管猫是不是能够听得懂,羽生纪泽听了一会儿,哼笑一声:“你养只猫,跟养个孩子似的。”
桑名真轻轻一笑:“你养弟弟,我养猫,不是很正常的吗?你不觉得小猫咪的叫声和人类的婴儿很像吗?就和人类听见婴儿的哭声会心软一样,听见小猫咪的叫声,也会忍不住怜爱的情绪。”
婴儿的哭声?
羽生纪泽下意识回想了一番,随即皱了皱眉,他好像没怎么听过婴儿哭声?
弟弟小时候有需求了也不怎么哭,都是哼唧几声,或者动一动手和脚来提醒他。
这个念头在羽生纪泽的脑海里一闪而过,他很快将注意力放在正事上来,等他逻辑清晰地将与琴酒相见的经过以及琴酒会在一天之后带他去某个地方的约定都告知桑名真之后,他问道:
“两年前,是琴酒联系的你吗?”
桑名真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设想该如何措辞:“其实也算不上是联系,他只是用特殊的方式留了一条消息,然后正好被我检索到了而已。”
他曲起腿,神色极为平静:“你那聪明谨慎至极的弟弟从来都见不到我,却早已察觉到了我的存在。所以,在你与他的再次相逢中,你已经知道了两年前的尼格罗尼死亡事件是他设下的谋局了吗?”
他没有任何要对羽生纪泽隐瞒的意思,只要羽生纪泽开口问了,他从来都是如实以告,但相反的,若是羽生纪泽自己不曾问起,他也绝对不会多言哪怕一句话。
桑名真与羽生纪泽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决不能单纯只以一句“朋友”来形容。
因此,即便两年来他看多了羽生纪泽因为琴酒两年前罗织罪名并射杀他而耿耿于怀,但他也从来没有在羽生纪泽不曾问起的情况下揭露些什么。
“我猜你的下一句应当是要问我为什么不早点说?”桑名真呵笑一声,“我可以直接回答,因为你也从来没有问过我啊!”
的确是郁气满盈想要质问的羽生纪泽心头一梗,忍着不忿道:“那你对他私底下在做什么有猜测吗?”
“你不是从小认证,弟弟是个小天才吗?”桑名真微微挑眉,无可奈何道,“我只是个普通人而已,没有你的敏锐,也不会所谓的探查,连你都不知道的事情,我又怎么会知道呢?”
羽生纪泽:“”
他缓缓吐出一口气,使他有些心急了,桑名真的确是不太可能知晓琴酒的秘密的。
所以,他还是需要等到一天之后,等琴酒将他带去他口中的那个地方之后,他或许才能摸出来一些他所不知晓的秘密,得到新的线索。
金吉拉敏锐地感觉到他的心情似乎不太好,四肢一蹬就跳跃到了羽生纪泽的大腿上,黏糊糊地蹭蹭脑袋撒了个娇。
一只手挠着猫咪的下巴,舒服得猫咪打起了小呼噜。
在他的沉默之中,桑名真用一种别有深意的眼中看了他一会儿,随后好似不经意地问道:“我还记得两年前第一次踏上这个岛国的土地上时,你还在说我有着一颗机械之心,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觉得,我的机械之心是不是更加人性化了一点?”
长发男人没有轻蹙,回想起两年间桑名真的经历,对桑名真为什么会这样问有些不明所以,他回应道:“有吧。”
桑名真暗叹一声,面上却不为所动,他点燃了一支雪茄,随意的模样好像他只是一时兴起的随口一问,随后又道:“既然一天之后你们还会再见,也许我可以给你一个提醒。”
或真或假的情绪掩藏在他的略微神秘的笑容之间,竟然与羽生纪泽有了一些神似。
“如果你要探清琴酒身上的秘密与矛盾,那就彻底抛开你眼里对他弟弟的滤镜,不要被血缘的关系蒙蔽眼睛,然后你才能看见你从来都注意不到的真实。”
他有些慨叹地吐了个烟圈,指尖微弹:“我以为你能戒断这杯名为亲情的毒药,结果你目前还是一个瘾君子。”
但如果不是这杯毒药的存在,他早就在最开始遇见羽生纪泽的时候,就已经丧命于他之手。
在中文里,桑名,与“丧命”同音,而所谓的“真”,又到底是他想要那一部分为“真”呢?
比起羽生纪泽这个没有任何意义甚至取的草率的名讳,桑名真这个名字,才是他对自己最大的矛盾。
“纪泽,不要自欺欺人。”
桑名真带着他的猫离开之后,羽生纪泽坐在办公椅上,手肘放在桌上,握起的双手抵在额前,闭着眼眸,恍若沉睡。
他的思绪徜徉在久远的回忆里,从他最开始在如血的夕阳里抱着一个还是婴儿的弟弟、一直到他带着弟弟辗转搬家到白伦街,并且一直在那里停留到弟弟九岁时,一切都好像很平常,没有任何异样。
他反倒是时常觉得自己天赋异禀,第一次带孩子就能够将弟弟顺顺利利无病无灾的带着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