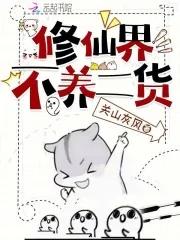风云小说>被我渣过的雌君他重生了惊兔 > 第13章(第1页)
第13章(第1页)
“……唔!!”
金发雄虫捂着鼻子,负气蹲下去,金眸哀怨地瞅着身边同样陪他蹲下来的男人。
“……我很想跟你做爱,”他直接说出小雄虫吭吭哧哧说不出的词,“可我感觉你很怕我。”
“谁怕你了,我怎么可能怕你!”
“好,那今晚我可以碰你那里吗?”
“………………”金发雄虫耳根红了个透。
艾克赛尔盯了漂亮的小耳朵一会,仿佛完全不知道小雄虫快要羞到冒烟了,继续问:“可以吗?”
“……你好烦!你为什么非要问我!又不是、又不是我说不能碰,你就不——不,不碰了的。”
西泽郁闷死了。结婚前,艾克赛尔根本不会这样问他问题,都是结婚惹的祸!
“不会,”艾克赛尔用低沉又有磁性的嗓音缓缓说着,“我永远不会勉强你。”
“…………”
这又是西泽没办法给出回复的话题。
他含着水光的金眸狠狠瞪了艾克赛尔一眼,凶巴巴道:“你不是要给我穿外套吗?你看,在你怀里都弄皱了——难看我就不穿了哼。”
“不皱。”
“你说不皱就不皱呀?你抖开我检查检查。”
艾克赛尔自然照做。
看着他紧绷的大块肌肉统统收力去展开外衣,西泽又略略满意了一点——嗯,在很多时候这虫还是很听他的话!
结婚好像影响也不大噢?他微微仰着下巴,像个大爷一样站起来、展开双臂,等男人替他将外衣穿上。
西泽喜欢穿好看又讲究的衣服,但他通常是站在那等机器人或小跟班为他穿好,他自己是不怎么会的。
他起初还因艾克赛尔那几句堪称冒犯的话不肯看他,余光瞥见男人面部表情严肃得好像在做什么了不起的科研实验……西泽翘了下嘴角,皮鞋尖踢了踢男人裤腿,故意问:“干嘛板着脸,不高兴做这些事吗?”
这种话他在过去十几年问过很多遍,每次都只有一个答案——
“不,我很高兴。”
男人说。
西泽哼了声,大方地不计较那些令他羞恼的话了。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在这颗‘玫瑰星球’上度过,甚至他和艾克赛尔的第一次——嗯,也是在玫瑰丛里。
那时艾克赛尔的精神海还没有崩坏,是个身体强健又刚得到雄虫的成年雌虫。他望向金发雄虫的目光有意无意带着‘求爱申请’,他知道小雄虫不懂这些,他很想教他。
雌虫不需要教,他们天生就知道怎么让自己在雄虫身上获得快感,这大概是一种不公平?反正西泽在前期表现出好几次强烈抗议——艾克赛尔总用那强硬到搬不动的大腿压住西泽孱弱且不经常锻炼的腿,虽然由西泽作为插入者,但艾克赛尔经常坐在他身上从头到尾掌控节奏。
艾克赛尔强到变态的腰力往往能把西泽欺负到哭。
这颗星球上的玫瑰有西泽两个手掌那么大,少刺,但朝里面一躺肯定会被刺到——
更何况艾克赛尔当时裸露着上半身,都不需西泽怎么抓他挠他,他后背自有一大块被刺划伤。有的刺扎得深,是哭红鼻子的西泽跪坐在床边一点点给他弄出来的。
艾克赛尔当时真是有点疯,明明该疼得要命,还逼西泽嚼碎了花瓣喂他,什么羞耻游戏都说得出口!
清雅好闻的汁液沿着不断啃咬、吸吮的双唇唇角落下,艾克赛尔大他一倍的手牢牢护在他腰间,偶尔还形成一股推力……
欲求不满的雌君果然最讨厌了。
-
前世他们在花海里做了多少次,回飞船又多荒唐——几个春梦反复交替,可想而知西泽醒来时是个什么状况。
他黑着脸掀开被子,鞋也不穿就往浴室里跑。
趴在被子上边的小怪物险些翻下床榻,幸好前肢反应够快死死勾住床单,尾巴一摆,极其迅猛地跳了回来。
正好落在小雄虫睡过的地方。
短圆鼻头微微耸动,嗅到仍有余热的床面残留浓浓诡异又熟悉的味道,登时红眼一亮,鼻头下意识戳进床单里——
整个怪物如被具象化的气味纠缠一般在这块热热的地方翻滚着,恨不得将床单撕下一块裹满身体。
它亢奋得身上大半鳞片都发烫翘起,将本就微皱的床面搅得一塌糊涂。
事后略略冷静下来,又神经兮兮用爪子慢慢抚平,结果没有收好的尖钩差点扯破绵软脆弱的床单。
它盯着快要破掉的地方呆了会,眼中掩不住的暴躁似乎很想就此将整个床榻腐蚀,这样就不会被小雄虫看见了。
——最后,尾巴小心翼翼顶着被子盖住这块,它若无其事爬回枕边团成一个椭圆,只露出三只猩红的小眼睛凝视浴室门口。
它躯干所有鳞片都染上小雄虫那种东西的气味,这个姿势正好可以供它悄咪咪舔舐。若它这张覆满鳞片的脸能做表情,此刻该一脸叫虫惊悚的痴迷。
-
微微发红的指尖郁闷划过腰间没有消退半分的黑色长印,尚还稚嫩的身体仿佛根本承受不住如此迅猛的印记,每次映在镜中都会娇弱可怜地发出无声哀鸣,瑟瑟祈求谁将它赶走。
金眸恶狠狠地瞪着黑色长印,软红的唇小幅度开合,像一碗黏黏糊糊的玫瑰花露,光是看着就让人感觉甜和香:“再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你消不掉,我就去找讨厌的医生。”
他如此认真地威胁不会说话的黑色长印,希望它这么大个东西能识相点。
西泽喜欢泡澡,总泡得浑身发红、困得不得了才被雌君抱出来擦干,再用香香软软的小毯子一卷轻轻放到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