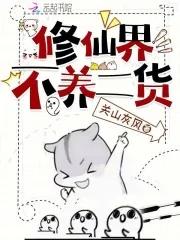风云小说>温染纪宴珩在线阅读 > 第80章 相好的是不是哥哥(第2页)
第80章 相好的是不是哥哥(第2页)
“原来母亲在这里。”房门敞着,纪宴珩没敲门,径直迈进卧室。
温染脊背僵硬,没回头。
“您先和她聊,聊完我再聊。”
纪宴珩神色从容,姿态悠闲,翘起腿,脚尖微微晃荡着,目光掠过温染,她屋里热,又紧张,鼻头一层汗,面颊粉扑扑的。
他开口,“关门。”
温染浑浑噩噩,反手关严。
纪夫人被他打断,心情不佳,侧目瞪他,“深更半夜了,你聊什么?”
“我和您聊。”纪宴珩手搭在膝盖,时不时戳一下,“我带着她去医院了。”
温染一颗心险些蹿出嗓子眼,她诧异盯着纪宴珩。
“去干什么。”纪夫人不逼温染了,开始逼他,“孙太太没多心,不代表她以后不琢磨,假如琢磨出个门道儿,你父亲和我苦心经营的纪家,包括你的婚姻,要全盘毁掉。一旦菁菁的大伯堂叔问罪纪家,你怎么交待。”
“您在说什么?”纪宴珩一脸茫然,“染儿去做婚检,您扯什么华家。”
他手里攥着一份化验单,搁在梳妆台上,“世清的情史不少,有规规矩矩谈的,有短期玩玩的,万一染了什么脏病,怪染儿,怪纪家,那可是一桩冤案了,有这份报告,可以堵耿家的嘴。”
纪夫人一愣,抓起报告单,果真是婚检报告。
纪宴珩似笑非笑,“母亲还有疑问吗?”
这副局面,搅得纪夫人瞬间无言以对。
“染儿婚检,世清带她去,我也能带,你当哥哥的出面不合适。”纪夫人没那么严肃了,好声好气的。
“世清要是心虚呢。”纪宴珩放下翘起的腿,端正了坐姿,“耿家在医院是有人脉的,我不相信他的报告,我只信我亲手拿到的。”
纪夫人瞥温染,“你总是支支吾吾的,做婚检害什么臊啊。”
温染几乎把毛巾揪烂了,手心全是汗。
她不晓得报告单从哪来的,下午在医院抽血,拍片,验尿,一系列的化验,估计纪宴珩从中安排了。
纪夫人起身回主卧,纪宴珩跟着。
擦肩而过的刹那,他停了一秒。
温染一口气悬在胸腔。
男人没讲一个字,凝视走廊的灯影。
熏黄的光洒下来,纪宴珩有一抹微醺感。
他旋即出去。
。。。。。。
纪淮康次日傍晚回来,一边脱西装,一边听纪夫人念叨。
“宴珩越来越荒唐了,我准备接菁菁来老宅住。”纪夫人泡了一杯花茶,递给纪淮康,“无论宴珩解释得多么合情合理,我照样不踏实,菁菁住进来,朝夕相伴,宴珩慢慢会收心的。”
“随你吧。”纪淮康喝了一口茶,他另有心事,“当初收养染儿,一则可怜她,二则我们膝下无女,想要一个女儿。染儿和耿家联姻,虽然对宴珩有好处,可为了宴珩,牺牲染儿的幸福,我考虑了几天,不如算了吧。”
纪夫人本就烦躁,纪淮康一打退堂鼓,她更恼了,“这八年,我娘家出资供养染儿母女,我请名师教染儿弹琴,唱戏,跳舞,培训她礼仪,下棋,茶艺,连一双袜子都是名牌,我凭什么白费精力?我给她最优质的生活,她回报我是情理之中。何况纪家救了她的命,否则她流浪街头了,她母亲也病死了,小恩小报,大恩大报,有错吗?”
纪淮康额头夹出一缕缕皱纹,没吭声。
他主外,纪夫人主内,在外,她服从,家里,他服从,分工明确。
纪夫人的社交手段是一等一的,结婚三十多年,夫妇没吵过架,作为李氏家族的长女,纪夫人强势惯了,他劝不通。
“叶家找过我了,有意重新撮合柏南和染儿。柏南一表人才,品行贵重,其实——”
“我娘家不缺钱。”纪夫人一口拒绝,“叶家有钱,嫁柏南是锦上添花,耿家有权又有钱,嫁世清是雪中送炭。”
纪淮康彻底不吭声了。
温染站在玄关换完拖鞋,走进客厅,贴着大红喜字的木匣、木盒、木箱,摆满了茶几。
木匣和木盒是耿家的彩礼,房产证,珠宝,支票,一应俱全。
木箱是纪家的陪嫁,金器,车钥匙,正中央的一顶水晶头冠在灯光下熠熠生辉。
是纪宴珩亲自挑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