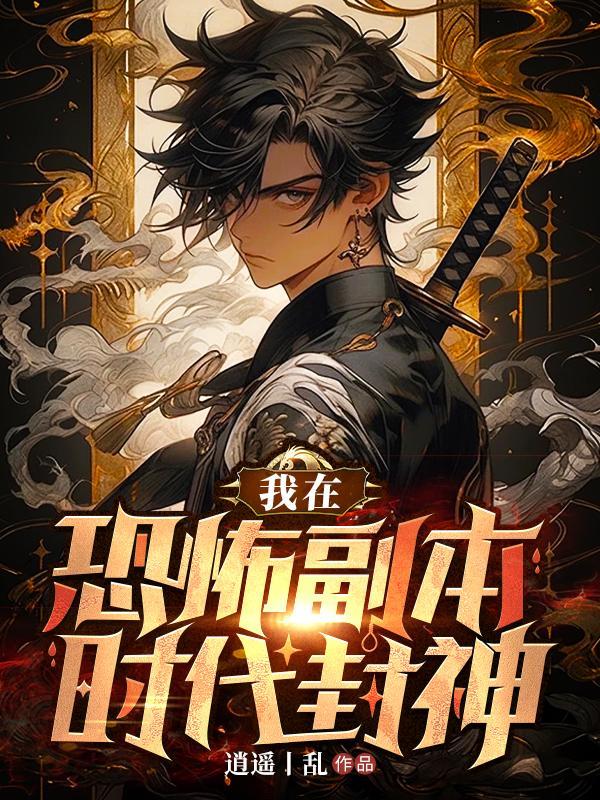风云小说>阳春白雪打一准确生肖 > 第19章(第1页)
第19章(第1页)
苏词俯瞰这状元楼下的近景,瞧着街市上几个十余岁的少年郎嬉笑打闹着走了过去,对于谢瑾的暗讽不置一词。
有些人生来便是如那春日里漫山遍野的杜鹃花般绚烂的,自己或许也曾有过那种时候吧,所以才会让谢瑾失望了。
他未变,只是自己变了。
“前几年,我认识一个人,同你很像,如果你们有缘见上一面,一定会觉得相见恨晚。”苏词干脆找了个合适的位置躺在在了这楼顶看这夜空深邃,星子闪烁。
一个是铁骑银枪的小将军,一个是红衣白马闯蕩江湖的少年郎,同样的炽热意气风发,也有着那样崇高到苏词觉得遥不可及的理想。
“世人都向往长安,可在我看来,长安有什麽好的。”谢瑾偏头看了苏词一眼,又继续饮酒,轻笑了一声,“乱花渐欲迷人眼,是这天底下最能改变人心的去处。”
他们自说自话,仿佛在回答对方但又好像从未聊到一处去过。
苏词一只手枕着后脑,翘着二郎腿的模样閑适,只轻轻地勾唇笑了:“怎麽愿意坐下来和我说话了?”
“你说的那个人是谁?”谢瑾却不知他什麽时候又认识了这样一个人,就像他不知道为什麽苏词要冒着危险去救下一个杀手一样。
“这几年,我父亲怎麽样了?”苏词又问。
“这麽多年来,我是怪你的,至今也是。”谢瑾长叹了一声,似是无奈,“不知道从什麽时候起,你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只想着你那琴,旁人说你是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
我却觉得你连季子牧都不如,甚至那些纨绔子弟都比你好。
因为,你不该是这样的。”
苏词闭眸掩盖自己的情绪翻涌,任由谢瑾说着话。
“可人生是你自己的,你爹娘你爷爷都默认了你现在的选择与生活,我又能如何。
或许是长大了吧。”谢瑾自嘲般笑了笑,“现在想来倒是觉得从前幼稚,总觉得揍你一顿能唤醒你的心气。
这些年,我虽然不在长安,但也不是耳聋心盲之人,这长安城看似繁华,有时候却是会吃人的。
虽然不知道你在做什麽,有些事却别自己藏着。”
这长安繁华,有时候却是会吃人的,苏词在心里重複了一遍他的话,随后坐起身朝谢瑾伸出了手,略带几分玩世不恭的笑挑眉道:“给我喝一口。”
真心待他的人不多,就这几个,苏词却不想将这几个人牵扯进来,少年意气也是将朋友兄弟看得比什麽都重,做起事来总不计后果。
两肋插刀,肝胆相照的坦蕩心思苏词是没有了,这具看似清风明月的皮囊之下也充满了算计。
他们有他们的家人朋友,不该为了一个人而将一群人置于险境。
苏词从谢瑾手上接过酒坛子,仰头豪饮了一口,用袖子肆意地擦了擦唇边的酒渍,不疾不徐的语调缓缓开口:“听说草原上有一种花,叫做格桑花。
不似世人喜爱的花那般花团锦簇,也不如兰草高雅。
同野草一同生长着五颜六色,花期漫长。
也同野草一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是啊,边塞和长安不同。
许多时候条件艰苦你却觉得自在快意。
落日也与长安的不同,便是你读王维的那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也是只能想象而已,却不如亲眼所见的万一。”谢瑾的话茬终于和苏词接到了一处。
“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自然该做那边塞的雄鹰翺翔于九天。
你什麽时候回去?”苏词将酒坛子递回给了谢瑾,谢瑾没接。
“这酒水太过寡淡,不适合我。”谢瑾拒绝道,“过两日便啓程。”
“替我带封信吧。”苏词斟酌过后还是说了句。
“你这两日遣人将信送至我府上便是。”谢瑾又像是想起来什麽似的,“这麽多年,苏伯伯从未收到你的一封信过,怎麽突然想要我为你带信了。”
除了你,其他人不合适,苏词心道,不过却也未明说:“或许是心血来潮。”
谢瑾看着苏词摇了摇头:“都道你是长安第一琴师,此次分别也不知什麽时候才有缘听你抚琴一曲。”
“你知道,我的琴音不与不识音律雅乐之人听。”苏词笑着拒绝道。
谢瑾被苏词的言语一噎:“好听不好听我还是听得出来的。”
“在你耳中只怕这长安城中的乐师每一位演奏都能得到一个好听的评价,又有谁是真正‘呕哑嘲哳难为听’的。”苏词不可置否。
只见这状元楼下忽然热闹了起来,阵仗像是来了一位讲究排场的王公贵族。
谢瑾像是瞧见了他不想见的故人一般,起身的时候罕有的慌乱险先踩碎了别人家的瓦片:“苏词,多谢款待,今日我便先走了。”
谢瑾施展轻功,在房檐之间轻踩,似是乘风而行很快便消失在了夜色里。
“诶。”苏词慌忙起身还来不及叫住人,只看着人的背影逐渐消失,轻声补充了一句,“你倒是先带我下去啊。”
我堂堂镇国公府的世子爷,虽然名声不大好,但也总不能站在这状元楼顶高呼救命吧?
苏词的心情又烦躁了几分,抱着酒坛子百般斟酌过后还是让暗卫将他带了下去。
苏词抱着酒坛子站在街市上往状元楼里瞧去,不禁叹气:季子牧他们不知道还在不在,总之自己还要去结账。
苏词上了这状元楼在楼梯口见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忽然清楚谢瑾为什麽逃也似的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