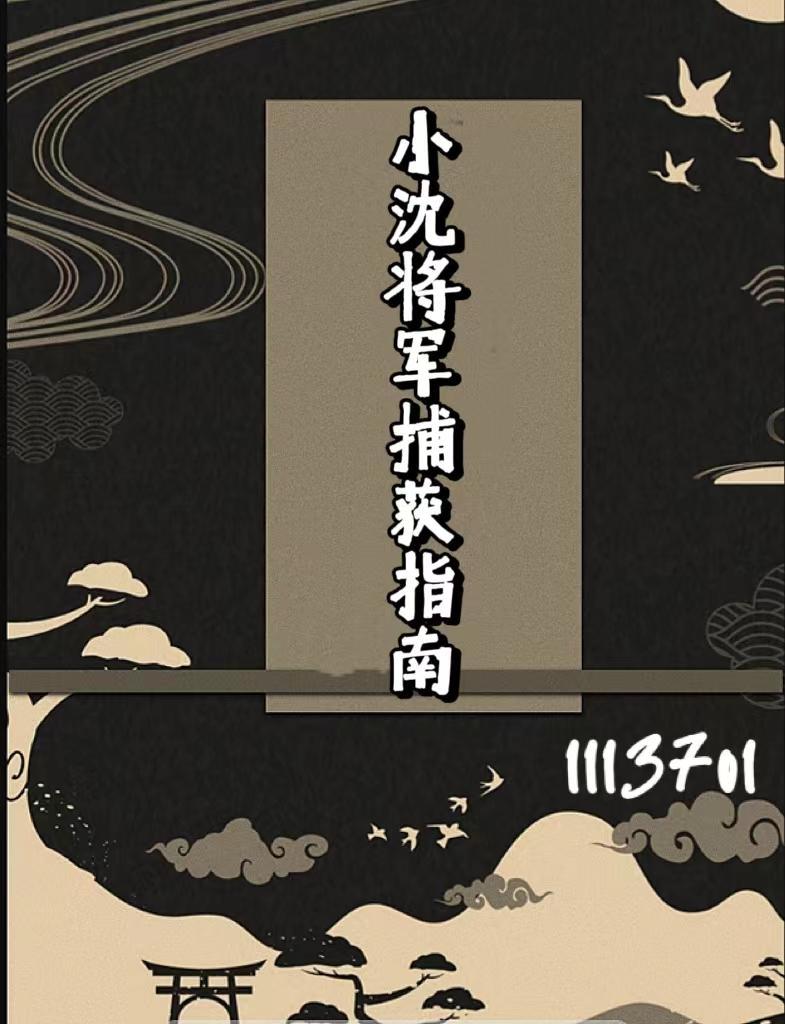风云小说>明决子图 > 第15頁(第2页)
第15頁(第2页)
施世朗閉上嘴巴後,明決的耳根總算是清淨了。
他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出去,便靠牆稍作休息,略微平緩地呼吸換氣,以保存體力和這密閉里稀少的供氧。
過了一陣,在幽暗混沌之中,明決感到有人靠近了自己,下意識皺了皺眉。
「你做什麼?」
話落,那陣異樣的體熱霎時離他遠了些。
緊接著,施世朗的聲音在他附近響起。
「沒做什麼,醫生說我感冒了,不能受涼。那邊冷,我往這邊挪挪,太黑了沒看見你在這裡。」
「是嗎?」明決抿了抿唇講,「施大畫家不是來看你今天滿三歲私生子的嗎?」
他說完以後,施世朗沒有接話,不清楚是不知如何應對他的拆穿還是別的什麼。
明決沒有理會,往旁邊挪了一步,離他遠了些。
大概過了幾分鐘,闔著眼睛的明決又感受到了那陣怪異的體熱。
他不想和施世朗再浪費口舌浪費氧氣,便繼續往旁邊挪了一步。
還沒過去三分鐘,那陣溫熱又覆了上來。
明決想要開口,話到嘴邊還是忍住了,又往前邁了一大步。
可那陣熱就像香口膠一樣粘著他不放,怎麼也甩不掉。
如此兩三次後,明決忍不住了,皺著眉喊他的名字。
「施世朗。」
兩三秒過去,沒有人回應他。
明決無話可說地搖了搖頭,邁開腳步又要往旁邊走,鞋尖還沒著地,冷不防被一雙有力的手抓住了臂膊。
「你別走了。」
施世朗低聲求他:「就一會。」
明決很是嫌棄地在微亮中回過頭來,忍耐了一陣後,無言以對地平了一口氣。
大男人也怕黑。
他把邁出去的那隻腳收了回來,無計可施地仰靠在電梯廂壁上。
爾後,在寂靜昏暗的狹小空間裡,他感覺到一張柔軟的臉伏上了他的肩膊,貼著他的襯衣,一下接著一下,很輕很輕地呼吸。
明決稍稍抬起了臉,看著轎廂上方那沉寂失靈的照明,平靜無言地眨著眼睛。
這一邊,施世朗察覺到明決不再走了,懸著的心終於放下,使勁抱緊了這根救命稻草。
他怕黑的毛病,是小時候落下的。
在他還很小,他家老頭還沒有發跡的時候,他們一家三口就住在海港邊一個很小很破的鐵皮屋裡。
那時候,他們家窮到連電費都交不起,三天兩頭就會被斷一次電。
記得那是一個很炎熱的下午,他家老頭出去找人借錢。他坐在床上,看著他的媽媽在屋裡焦急地來回踱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