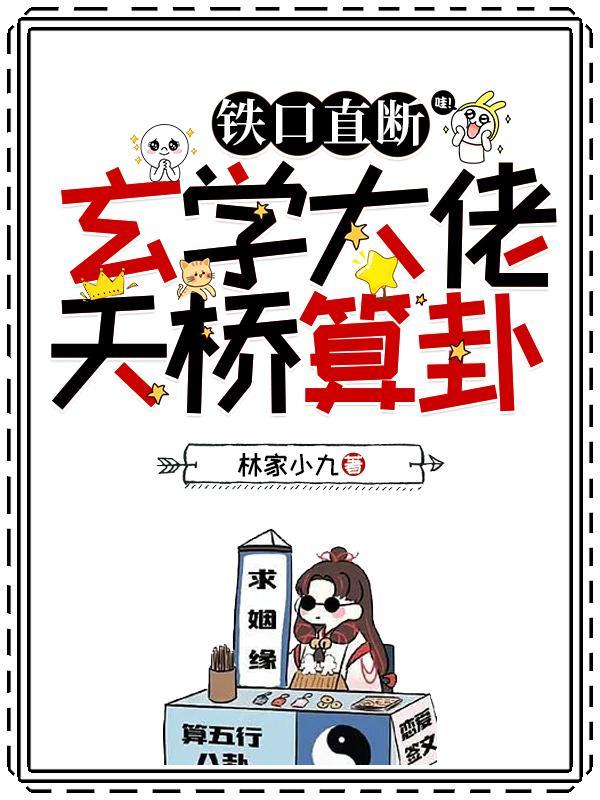风云小说>夫君他貌美如花格格党 > 第86章(第1页)
第86章(第1页)
>
李牧:“来人,禁军统领高慎居心叵测行刺天子,暗害太子,买卖官职种种罪行证据确凿,数罪并罚,即日起押入天牢,择日再行处决,削去高家国公世袭一爵贬为庶民,抄没所有家产一律充公。”
高慎还想挣扎,就听见外面士兵整齐划一的铁甲刀兵相撞的声音。玄铁营的甲胄竟然出现在大殿之外。
雷信声如洪钟:“高统领还是束手就擒为好。”
楚寄远道:“陛下,嫔妃高氏也是高家女,不知陛下打算如何处置?”
高慎一愣,浑身僵硬地被侍卫按住,狼狈不堪地瞪着楚寄远。
李牧冷冷道:“高氏入宫多年,且育有皇子,降为才人,即日起禁足永安宫。”
今日种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高氏猖獗,天子雷霆手段下安能幸免,不过是早晚罢了。
鼎盛一时的国公府在帝王的三言两语间覆灭,所有人都低垂着头战战兢兢,生怕遭受池鱼之殃。
夏日就要到了,天空中突然狂风四起闷雷阵阵,伴随着一道白光闪过,大雨倾盆而下。
林野疾步走入雨中,身后欧阳越替他撑着伞:“大人,高慎卖官鬻爵的证据出现的太突然了,这分明是有人想借我们的手除掉高家,就算陛下让我们暗中查高家的罪证,可我们羽林卫也不能成了别人的幌子啊,这件事我们要不要告诉陛下?”
林野:“事情没查清之前什么都不要说,这件事你暗中去查,能把高慎的罪证悄无声息送到羽林卫来的,只有我们羽林卫自己人,记住,不要打草惊蛇。”
“是。”
纪风的剑在阴沉昏暗的雨天里亮的晃眼,一个身着黑色飞鱼服的校尉连滚带爬跌倒在雨中,满眼都是恐惧。
“饶……饶命……我我是替……”
削铁如泥的长剑手起剑落轻而易举就划破了人的血管,喷洒出来的鲜血在瓢泼大雨中很快消失无踪,没留下一点痕迹。
……
贺景泠一身白色素衣站在廊下,雨中带风,丝丝缕缕地吹到他的脸上,不冷,但身上就是无端的凉。
那张苍白的脸上额角有一块醒目的墨迹,被风吹乱的乌黑的发随意垂落,四周安静的只听得见雨声,雨水打在伞面发出了声响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李长泽一身墨色常服衬得身材高大笔挺,肩膀宽阔身高优渥,没有了刻意掩饰,一步步走来时伴随的压迫感让人不敢直视。
他看着贺景泠时的眼神深沉而又平静,唇角忽地挑起一抹笑,他执伞走到廊下:“怎么站在这儿?”
贺景泠静静注视着他,轻声道:“等你呀。”
他说的煞有其事,神色自若,李长泽却敏锐地察觉他似乎心情不是太妙。
祝安从另一边拿着披风跑过来,看到李长泽下意识止步,咽了咽口水,慢腾腾地挪过来:“公子……”
祝安刚要跟贺景泠说话手中披风就被人夺了过去,李长泽不紧不慢替他系好带子,一本正经看了看,满意道:“可以了,走吧。”
贺景泠对祝安道:“我跟他走一趟,你和狄青就留在府中不用跟着了,”
祝安不高兴地撇撇嘴,一副不想答应的样子。贺景泠继续道:“他身边有纪风和卢飞,你在家乖乖听话,看好阿呆,别又去隔壁掀瓦了。”
李长泽不轻不重地哼笑一声,眼神上下打量着祝安,祝安手心有些汗,他在腿边擦了擦:“……好。”
祝安脚底抹油跑了。李长泽再次打开伞走进雨中,贺景泠跟着他走到伞下,夜色与黑色的披风融为一体,那双眼睛漆黑又平静。
“在想什么?”李长泽问。
“在想……”贺景泠平视前方,“高慎现在会想些什么。”
李长泽笑了下,眼底一片冰冷:“他肯定在想自己怎么就一夕之间一败涂地了的,只是他太蠢,就是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自己到底是为什么会败。”
贺景泠:“卓小宛从他书房里搜出的大量他买卖官职的证据,若不是他们三番两次派人追杀,我还真没法从这几批刺客里面找出共性来。”
风突然大了些,大而密的雨噼里啪啦砸下来,溅湿了他们的衣摆,李长泽不动声色把伞朝贺景泠那边偏移了些:“一些毫无逻辑的刺青,偏偏你猜到了它们是组合起来的高家诏令杀手的私印。”
“谁让我聪明,”贺景泠侧眸看了李长泽一眼,“照着卓小宛给的令牌样式一对比,同样的刺青刺上去,高慎怕是自己也不知道猎场的死士究竟是不是齐王背着他派去的。”
这场局他谋划太久,从一开始的董伯远,南宫烁,到现在的高慎,他亲手把当年那场败仗中的得利者一个个从高位之上拉了下来,一切似乎都在朝他最初预想的地方前进。可他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高兴。
李长泽不知道的事,他知道,他一直都知道当年大齐接连战败的真相,知道为什么一个征战沙场的将军为什么最后会落得那个结局。
他们这些人,不过都是上位者的棋子,赤胆忠心抵不过尔虞算计,他只想尽他所能,保护他想保护的人。
贺景泠一时恍惚,他回来这么久,至今连贺元晟的面都没有见过,长兄如此,想必是真的恨极了他。
亲人反目,流言在身,贺景泠偶尔想,或者他确实不该回来,卷进祈京城的是是非非中,天下之大,他本可以安乐如意的过完这一生。
贺景泠想的入神,没注意到脚下还有一级台阶,一下踩空了。李长泽眼疾手快拉住了他:“想什么呢想这么入神,路也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