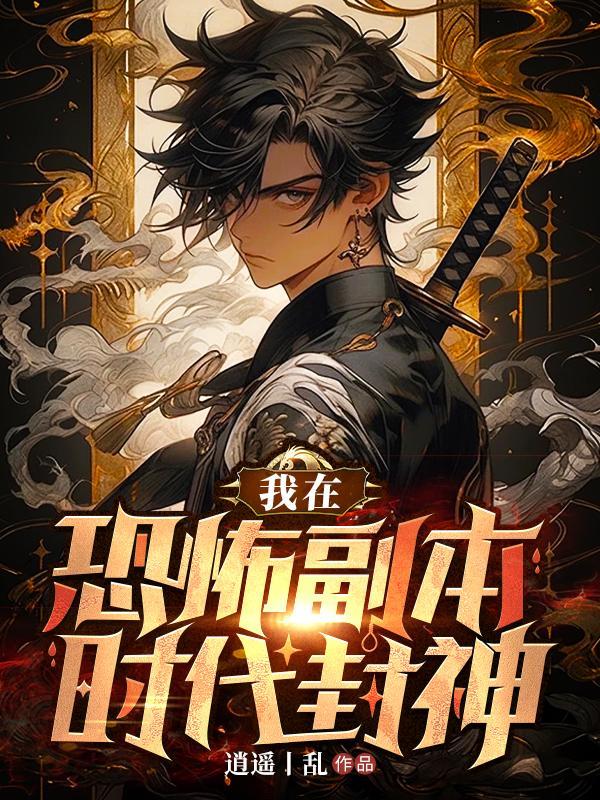风云小说>雾夜新婚妄云栖全本完结 > 第五十三章 狩獵者(第5页)
第五十三章 狩獵者(第5页)
她微笑著,嗓音稍稍發著顫,也沒有回答她的問題,而是用了小時候給她講故事的口吻,低低開口。
「我懷上你三個月整的時候,做了一個夢。」
「你想啊,你是十月的生日。我懷你三個月的時候,正好是寒冬臘月,雲珀的雪可大了,大得人睜不開眼睛。」
「可是,在那個夢裡,我走在春天的山上,漫山遍野都是桃花樹,粉色白色的花瓣被風吹著往下落,也跟下雪一樣。」
「那雪落在身上,卻暖洋洋的。」
「是暖雪啊。」
將近過去了三十多年的一個夢,她還記得這麼清楚,就好像眼前也看到了粉白相間的挑花似的。
柳韶笑意更深,又道:「我一直往裡走,走到一棵最漂亮的桃花樹底下,看到一個四五歲的小姑娘。」
「小姑娘嗓音可甜了,一見我,就叫我媽媽。」
柳韶淚光閃爍,唇邊卻仍笑著,看向她時,嗓音發顫。
「孩子,從那個夢裡醒來之後,我忍不住地一直哭。」
「我不想讓你走,我想把你留下。」
茶杯由燙轉涼,許多年的時光從眼前掠過。
柳拂嬿望著杯里的茶水,想起柳韶帶她去看婚紗,柳韶送她漂亮的手鍊。
想起柳韶騙她去掃墓,其實是又去了緬甸賭玉,又一次欠下巨債。
債主們無處不在,到處逼債,無論是學校還是家門口,只要見到她,就一定會說很難聽的話,會弄壞她身上帶的東西,摔壞她的畫具,破壞她重要的考試。
從那以後,她戒備心極重,又自厭自棄。
然後,現在,柳韶又給了她的回憶。
桃花樹夢境的回憶。
柳拂嬿喝盡了杯中的冷茶。
她不是不記得,柳韶濫賭、拜金。
可如今才知道,柳韶把她這個女兒的生命,看得比這一切都更重要。
可那又如何呢。
她儘管關心女兒的生命。
卻並不曾更多地關心女兒的感受,關心女兒內心深處的那些哭喊。
柳拂嬿不知道,其他人的母女關係,是不是也像自己這樣矛盾而複雜。
她望著空空的茶杯,彎了彎唇,說不清眸色是冷是暖。
只是淡聲道:「你要是打掉我,就沒有後來的這些事了。」
「是啊。」
柳韶蒼涼地笑了笑。
少頃,又長長嘆息一聲,道:「可是,我要是打掉你,你現在就不會坐在這兒,叫我媽媽了。」
柳拂嬿摸了摸自己的右腕。
那裡的疤痕已經很淡很淡,幾乎看不見了。
她想了一會,捲起長袖,露出自己的手腕。
手腕上,完好無損的金綠色手鍊,發出玎玲作響的清脆聲音。
見狀,柳韶睜大了眼。
「你看,它之前不是摔斷了嗎?」
柳拂嬿低聲開口。
「我又修好了。」
「從那以後,還是一直都戴著。」
-
在秋天即將走到末尾之時,傳出了6皎和薄崇離婚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