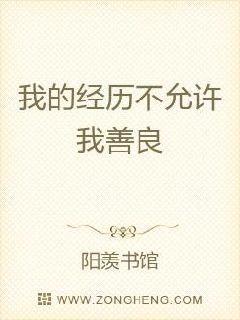风云小说>阳春白雪和曲高和寡的区别 > 第64章(第1页)
第64章(第1页)
虽然衣食不缺,但这样狭小的方寸之地,又不怎麽见得到外面的阳光,除却每日狱卒照例送饭过来,连个人都见不到。
又怎麽不寂寥?
苏词在宣纸上写了许多字,翻来覆去只两句诗而已:希君生羽翼,一化北溟鱼。
也不知他如今怎麽样了,此生应当是不能相见了吧?
这麽久的时日不见自己,他也当真是狠得下心。
后来的是林悸,
正在风头上,他也敢来,要是被归为自己这一派的,怕是与那个位置无缘了,苏词不免说了他几句。
“我说过,坐在那个位置上也并非天下第一爽快事。”林悸手摇折扇一副事不关己的姿态,“今日我来,是与你把酒言欢不醉无归的。”
林悸手中拎着的是两坛竹叶青,将酒坛子往桌上一砸,啓封的那一瞬间酒香四溢,虽身在囚笼之中,二人相视一笑,在这一刻都觉得无比的自在。
林悸说看着自己像是看着铜镜一般,苏词亦然,世上是有那麽一种情感无关血缘无关风月,唯有相知而已。
落到如此境地,功名半纸,风雪千山的又何止那些文人仕子。
“这世上,论洞悉人心没人比得过他。”林悸说的那个他指的自然是就是皇帝,“当初或许应该如你所说的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林悸指的是当年苏词提议的逼宫。
“我是在利用你,殿下,没有苏词您也能成大事。”苏词摇了摇头,有些人天生就有帝王气,凭着林悸的各个方面的能力,若是皇帝不糊涂,未来那位置也该是林悸的。
“什麽才算是成大事?”林悸反问,“名垂青史?
苏词,责任和理智告诉我我应当去争,可我心知我如果成了并不一定会高兴。”
既然林家人受天下奉养,这便是他该担的责任,林悸原本是享受权力给他带来的乐趣的,直至遇见了苏词。
有道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这样的人本该是鲲鹏,却困于这方寸之地,时也命也。
“你若不是苏家人该多好。”林悸无奈地豪饮了一口酒,带着几分醉意的说法。
“殿下,只有苏家的苏词才是苏词,过往的一切但凡有丝毫的改变,我都不会是现在的我。”苏词从不后悔生在苏家,死又何惧。
“殿下,我想这中原大地再无战事,百姓安居乐业。”苏词想要林悸的一个承诺,他是自己看中的人,继承者由他坐上那位置是再合适不过的。
林悸意动,听到这样的言语他并不兴奋,反而带着点哀伤:“若有那麽一日,本王会为你们苏家正名。”
苏词起身整理过衣衫跪下往地上重重地一叩首:“那苏词便在这里先谢过王爷了。”
林悸没有去扶他,心知此刻他该受着这一叩首,只看着他起身而複坐下。
两个人饮酒饮到兴头上,苏词击筑而歌,所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複还。”
都说筑音悲壮,如今更多了几分哀婉。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稼轩想收拾山河,可苏词又怎麽不想成为将军呢?
如今的心境与游离初遇那日已是大有不同却又可以预料。
这样慷慨悲歌的乐器的确是该失传了,有些不大吉利。
错了,错了,一步错步步错,从一开始这棋局都是必输之局,
苏词再小心谨慎身边还是被安插了人,那胡族大王身边的昭月公主,那假意投诚的禁卫军副统领……
皇帝才是执棋人,而自己不过是被围城的棋子而已,到底是输了。
这一夜,两人都喝醉了,林悸被他身边的小厮擡着出了牢房,而苏词拢了拢衣衫上塌便是呼呼大睡。
明日愁来明日愁,事已至此,也管不了这麽多了。
后来的是李文妍他们,
他们许是怕自己在牢狱中过得不好,带了许多吃的和用的来。
“苏伯伯的事我是不信的,我会请求陛下彻查此事。”季子牧依旧还是那个十余岁的少年心性,说他聪明倒也愚笨,哪里又懂得其中缘由,只知道一心为国罢了。
“不必了,你还不如以后多去我坟前同我说说话。”苏词略带苦涩的笑意含着几分无奈地看着季子牧,这麽多年来,许多人都变了,至少他守住了他的少年意气。
“你胡说什麽呢,天无绝人之路,即便是拼上这条命我也是要救你的。”季子牧一瞬间的恼怒说话语气从未这样兇狠过。
“那文妍怎麽办?”苏词无奈。
“文妍自然也是一样,包括谢瑾他们,我们怎麽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死,我做不到,文妍做不到,谢瑾陆川他们也做不到。”季子牧急切地反驳。
“不需要无谓的牺牲了。”苏词摇头,定定地看着季子牧,“你应该明白苏家为何会遭此劫难。”
“帝王术。”李文妍淡淡地补充了一句,不论对错,也不论你是否有反心,苏家的名声和权势威胁到了皇权,仅此而已。
苏词颔首,像是释怀地笑了:“这天下姓林,不姓苏。
你不是说我为什麽想选择成为琴师吗?我是真的喜欢雅乐,也是因为出入许多场所便宜上许多。
可有的事并非是我一己之力便能够力挽狂澜的。”
季子牧摇头,一脸难以置信红了眼眶眼泪将落不落的模样:“怎麽会?怎麽会?陛下他是明君……”
“他是明君,值得你忠诚的明君,你不要怀疑你的信仰,存远,只是他是明君和他做这样的事并不矛盾。”苏词看着季子牧的模样也是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