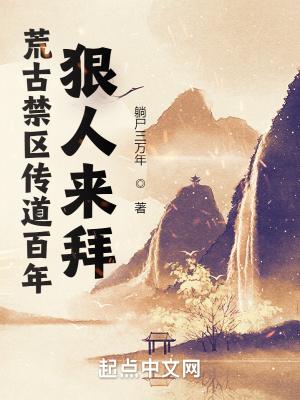风云小说>朕那个弱柳扶风的丞相大人 > 第38章 037不要臉的(第1页)
第38章 037不要臉的(第1页)
徐穎家,破堂屋之中。
全家都在,愁眉苦臉,茫然等待著世界末日。
昨天上午,費家惡奴已來過一次。
說徐穎打壞了費少爺,讓賠十兩銀子湯藥錢。又清算往年積欠的租子,加上滾動利息,一共折銀四兩七錢二分六厘。
家裡省吃儉用,總算養大幾隻雞,眼看著就能下蛋了,全被惡奴捉走抵債。
甚至,家中糧食也被奪走,讓他們今後無米下鍋。
惡奴們離開時說:「老爺仁義,允你們拖欠田租,便是少爺被打壞了,也不將你們逼上絕路。這般慈善的老爺,整個鉛山上哪找去?也算你們八輩子積德。老爺說了,再給你們一天時間,把剩下的銀錢湊足便罷。若是湊不齊,那就準備好田契過戶。咱家老爺真真善心,只要田骨,田皮還留給你家。今後可要記得老爺恩德!」
全家嚎啕大哭。
若按中國的劃分標準,徐家也曾富裕過,可評為「富裕中農」:有自己的土地,生活還算富足,但無力僱傭長短工。
但十年前,鉛山大災,旱蝗齊至。
徐穎的祖父、祖母相繼餓死,父親兄弟三人,帶著全家逃荒求生。
逃荒途中,徐穎的大哥、大姐、堂哥餓死,堂姐被賣給牙婆換糧食。徐穎的二叔也餓死,嬸嬸後來改嫁。還沒結婚的三叔,入山做了土匪,至今音訊全無。
幸而遇到好官,知縣笪繼良上任,立白菜碑,施粥放糧,以工代賑,徐穎全家總算沒有死絕。
回鄉之後,只能借高利貸種地。
利滾利,連利息都還不起,田產6續被收走大半。
一下子從「富裕中農」,變成半耕半佃謀生,還得打短工的「下中農」。
如今又遇這種事,看來僅剩的土地也要沒了,等待他們的結局是成為「貧農」。
……
「就不該讓三子讀書,老實種田哪裡會闖禍……」徐父臉上有傷,是昨天被打的,嘴裡反覆嘀咕著幾句話。
徐母無聲流淚:「總得有個念想,萬一考上秀才呢。」
徐父不敢反抗惡奴,只能責怪妻子:「秀才沒考上,倒闖了天大禍事。三子買書買筆的錢,還不如給浩娃娶親討媳婦!」
浩娃,是徐穎的堂哥徐浩。
二嬸改嫁時,不便帶著拖油瓶,就過繼給徐父餵養,今年二十歲了還沒成親。
徐浩老實巴交,性格有些沉悶,他說:「三弟打小就聰明,是該去讀書的。做了秀才相公,咱家就不用出役,我晚幾年成親也行。」
徐母低聲說:「要不去尋珍娘和姑爺幫忙?」
珍娘,是徐穎的姐姐徐珍,嫁給鄰村一個普通農戶。
徐父搖頭說:「珍娘能幫上什麼忙?她還沒出月子呢,這事莫要讓她知道。」
全家再度陷入沉默。
只有徐穎的弟弟徐茂,三歲小屁孩兒一個,還拖著鼻涕滿地玩耍,不明白家裡的天就要塌了。
左等右等,徐父出了堂屋,攏著袖子蹲在門口,遠遠打望費家惡奴的身影。
一直沒有出現,仿佛劊子手的刀,始終舉著不砍下來。
惡奴沒來,卻等來三個學童。
費如鶴穿著華貴絲袍,一看便知是富家少爺。
徐父自慚形穢,不敢與之直視,埋頭問候道:「少爺安好!」
不管是哪家的少爺,反正先問候總沒錯。
徐母卻認出他們,知道是兒子的同學,連忙回屋倒水:「少爺們請喝水。」
一路走來,費如鶴確實渴了,接過陶土碗就猛灌。他是尋機出來玩耍的,懶得管這種破事,對趙瀚說:「你來講吧。」
趙瀚將碗放下,拱手道:「見過伯父、伯母。」
徐父連忙起身,點頭哈腰,惶恐道:「不敢的,不敢的,少爺莫要折咱莊稼漢的壽。」
「少爺有禮了。」徐母竟道了個萬福。
徐母是見過世面的,年輕時在費家做丫鬟。因為意圖勾引老爺,遭主母掃地出門。先被許配給一個瘸腿老鰥夫,待丈夫病死後,才改嫁給徐穎的父親。
徐母行禮之後,忙問道:「穎娃……我家徐穎沒事吧?他已兩天沒回家了。」
趙瀚沒有說出真相,微笑安撫道:「徐穎無事,山長憐他聰慧,今後就住在書院裡。」
「那就好,那就好。」徐母終於放下心來。
徐父雖然埋怨不該送兒子讀書,但也只是口頭說說,心裡還是盼望兒子出人頭地。
甚至面對惡奴欺壓,要被收走僅有的土地,全家都不敢讓兒子知道,免得影響了兒子讀書的心情。他們也沒去含珠山,心想兒子躲在書院,總好過回到家裡受欺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