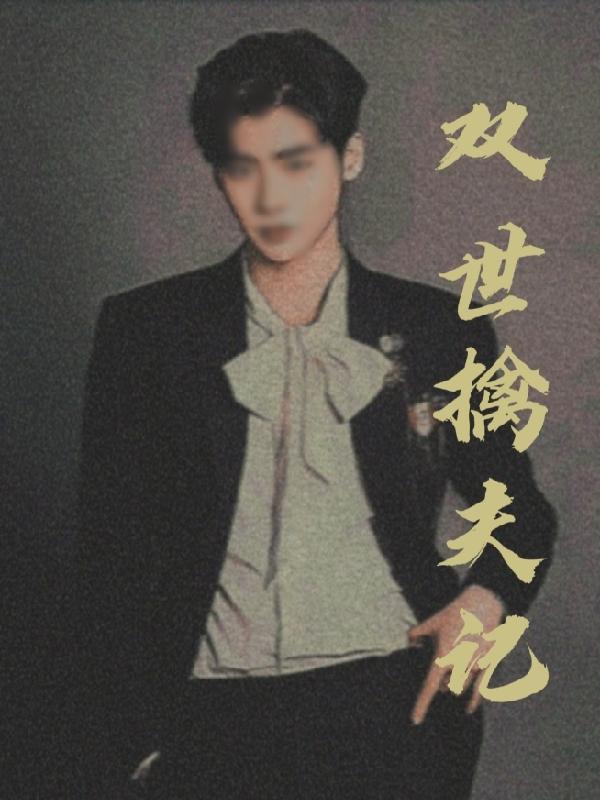风云小说>崩铁云上五骁我排第六笔趣阁 > 第34章(第1页)
第34章(第1页)
她迅速将桌子上的东西都扫进了口袋里。
景元“哦?”了下,但也止步于此,没再多问。他很快便恢复明朗顽劣的模样,摊手道:“卧病在家实在无聊,如今我母亲也大好了,我想来瞧瞧,什么时候能回云骑军效力。”
幼清道:“都说是半个月了…不还有三天吗?”
“奥…还有三天。”景元意味深长说了一句,他坐在她面前,翘起腿,把手放在脉枕上,幼清只好把手搭上他的脉,他的手大,幼清侧贴着他的手,就像被他握在掌中,如此相对,他声音也低了两分,“你的药够吃,就是在想什么时候复诊。”
“说了半月就会好,无需复诊。”幼清拉上他的袖口,和他说,“今天有风,罗浮天气似乎并无四季,但起风之时还是有些冷的,你不要着凉。”
“里头还有一件。”景元撩开衣领说,“阿娘为我缝制的里衣。”
幼清抿唇笑笑,将他的手推回去,景元道:“不知是不是怕我阿爹,这几天都没人来家里探望。”
这是在点她?
幼清躲闪着,景元的目光追着她瞧,她躲开他的追察,左右也不过十天没见,他真的记仇了?主要是一去他家,又怕被送什么惊人的东西,另外也怕…
怕自己不得不赴约,从他身边离开,看到他失落的模样。
幼清搓搓手,低着头,不想去看他的眼睛,怕他真的怪自己,更怕…他其实并不在意。
景元托着腮,神情放松,过了会儿,他用手碰碰她的胳膊,她抬起头,只见一只圆滚滚、胖乎乎的小鸟张开翅膀上下摇动,那小鸟立在他的指尖,稳住身体,便张开鸟喙,大喊着:幼清!幼清!
幼清双眼顿时亮了起来,她小心翼翼护住这只小鸟,它跳入她的手心,仰着脑袋,胸脯的羽毛白得像一碗牛乳冻,这鼓鼓的胸脯一起一伏,卖力地叫着她的名字,一看就是受人指点,拿来讨人欢心的。
幼清抱着小鸟,爱不释手地把玩着,奈何这鸟十分衷心,陪她玩了一会儿就挣扎着飞回景元肩头,用脑袋蹭他的头发,景元不知从哪里掏出一袋鸟食,小鸟在他肩膀探头,低着脑袋去吃,吃饱了才接着嚷嚷:幼清!幼清!
幼清笑得前仰后翻,这鸟是个破锣嗓子,说话沙沙的,听着好像一个老爷爷在扯着嗓子喊她,实在有趣。
她问:“还会说别的吗?背首古诗什么的?”
景元摊手道:“这也太强鸟所难了,我们也就认识了几天,还没来得及教。”
“实在对不住…”幼清憋着笑,逗他,“看来真是把你憋坏了,年纪轻轻都开始逗鸟玩。我刚才听你的脉,你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伤口我不必看也知道已经长好…就是左手不要握剑,这一阵子切忌吃力撕扯,让肉再好好长一长…”
景元耐心听着,唇边带笑,幼清懊恼道:“又开始唠叨这些了…总之你恢复得不错,走动自然是没问题了,既然你都来了,时间不早,不然我们去听听戏?”
他立刻赞同,似乎就在等着这句话呢,“行!去星槎海还是长乐天?”
“白珩上次带我去的长乐天。”
景元垂着眉毛说:“你和白珩都玩了,那我带你玩什么?”
“哎呀,再重复玩嘛,和不一样的人去一样的地方,感受也不相同。”幼清拉他起身,“走啦走啦,再晚一点就该没坐了,这次我们就盘个小桌子,不和人拼了。”
景元说着好,乖乖跟上她的步调,幼清给他买了一瓶浮羊奶,景元抱着奶说:“不来一瓶苏打豆汁儿?”
幼清赶紧摇头,“喝茶喝奶,不喝豆汁儿!”
他连声说着好,就这么跟在她后面,和她一起去了长乐天。
这里有处播幻戏的,还有现场唱词的,算是戏曲版音乐剧,他们来的时间尚早,还能抢到一个好位置,景元将买来的零食铺了一桌,又点了一壶茶和小菜,幼清问:“前几天白珩带我去你们云骑军训练的地方打靶子玩,我瞧瞧你们玩的也不过角抵斗禽,或者比比武力,文雅一点的便来听曲儿,时间长了岂不无聊?”
景元笑道:“因为玩乐时间少,所以不论玩什么都有意思。”
“怪不得…”幼清倾倒茶汤,与他说,“你们战事吃紧,但家中倒是一派太平呢。”
“毕竟这里是罗浮,并非曜青。罗浮作为舰队之首,自然要照顾四方,不会无止境地征伐。但巡猎的复仇永不停歇,仙舟舰队追逐丰饶余孽到星海之边界,不过此前也有孽物大举来犯,我们自然希望不要再出现这种事。”景元神色严肃了些,“若真会如此,你早日离开。”
幼清并不在意战争,即便现在开战,她也不会一走了之,便说了句:“这不是还没出这样的事?”
正在闲聊,厅内烛火熄灭,光芒聚拢,幼清看向台上,今夜是小姐书生的恋情戏,台下都是年轻男女,唱腔也现代了许多,虽说脱胎戏曲,可与舞台剧没什么区别,幼清还是第一次看这样又古又新的东西,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出戏景元已经看过了,他吃着桌上的零食,偶尔看向她,台上正在互诉衷肠,幼清见男女演员凑在一块,嘴唇都快黏上了,幼清躲开视线,低声吐槽:“哪有这么奔放的富家千金呢?”
景元笑了一声,显然是听见了。幼清不再看台上,把他们的歌声台词都当成了背景音,为了不影响别人观看表演,她还抬着椅子,靠近他坐下,景元道:“白珩都带你去哪玩了?”